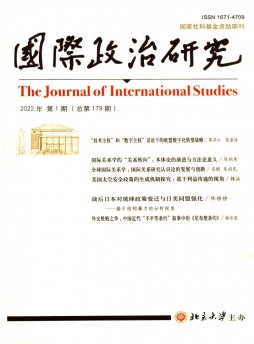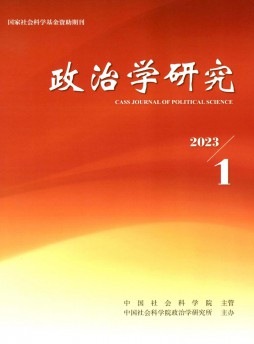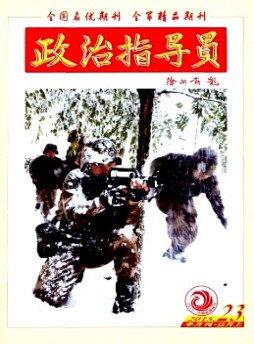政治生态下的“侠”文化剖析范文
时间:2022-11-18 08:46:57

[摘要]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侠”这一群体,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来自民间,将“侠”视为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千古赞许;而另一种来自官方,将“侠”视为“以武犯禁”的社会蠹虫,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这两种对立性评价的表象背后,却有着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即中国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民间对于“侠”的肯定性评价,是源于其在传统既有的体制和秩序之下无法收获公正时,对于体制之外的正义力量的期望和认可;而官方对于“侠”的否定性评价则是源于“侠”这种非官方的正义力量严重冲击了专制政体下的统治秩序。
[关键词]侠;义;法;政治生态;制度根源
千百年来,“侠”被看做是替天行道的英雄人物,受到无数平民百姓的称赞与传诵,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是百姓们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的不朽话题。但站在统治者的立场,韩非子却给“侠”以完全不同的概念,称其为“带私剑”、“以武犯禁”之社会蠹虫,建议君王将其斩尽杀绝。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似乎都采纳了韩非子的这一建议,对“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在传统的法律秩序之下,中国为何会产生“侠”这一文化现象,“侠”与“法”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为什么长期以来,民间社会和官方体制会对“侠”有着如此不同的评价?“侠”文化又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怎样的问题?这一切还得从“侠”这一概念入手。
一、“侠”之概念界定
有关“侠”这一群体的起源,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于“侠”这一群体最早进行概念界定的是韩非子的《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中将“游侠”与“私剑”并称,而带剑者的特征是“聚徙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2。这里,韩非子概括出了“侠”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有着高强的本领(以武);二是触犯现行法律制度(犯禁)。但这其中并没有对“侠”提出任何道德上的要求,似乎凡能够以武力触犯现行法律制度者———无论是替天行道之人还是鼠窃狗偷之辈———都可以归入“侠”这一群体。直到后世的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才对“侠”这一概念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今游侠,其行为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至此,侠的基本特征也被较为系统地勾勒出来:一是信守然诺(即其言必信,其行必果);“侠”者,一定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行,而绝不会自食其言,半途而废。如司马迁笔下的大侠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其信守然诺,重信重义,以致楚地谚语有云:“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而今日“一诺千金”的成语典故即是出自昔日的这位“侠”者。二是扶危济困(即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可以说,这是“侠”最为重要的客观特质,即凭借自身高超的本领和“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勇气,不惧危难,不避艰险,舍己助人,抱打不平,救人于危难之间,解人于倒悬之急。正如司马迁所言:“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史记·游侠列传》),每个人都有遇到危难、束手无策的时候,这种情况即便如大舜、伊尹、姜太公、孔子这样的仁者圣贤都不可幸免,何况是身处乱世的平民百姓?“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史记·游侠列传》)。因此,我们不难发现,“侠”的身影通常是出现在弱者遭受不公或身陷困顿、走投无路、求助无门之时。三是不求回报(即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可以说,这是“侠”最为重要的主观特质。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国家也有类似于中国“侠”的群体,即“骑士”。他们也会到处游历,助人解难和抱打不平,在客观行为上酷似中国之“侠”。然而,骑士做这一切的终极目的却是为获取名誉和财富。而“侠”在舍己助人之后,却是功成身退,不求回报。例如司马迁笔下的大侠朱家,为搭救被汉高祖刘邦所通缉的要犯,亦同样为“侠”者的季布,不惜以身犯险,挺身而出,四处奔走游说,终于救得季布的性命。然而,在获救的季布被刘邦所赏识,当上了郎中、河东郡守等高官,飞黄腾达之时,朱家却从此不与季布相见,羞于索取任何报答。因此,司马迁形容朱家乃是“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史记·游侠列传》)。信守然诺、扶危济困和不求回报,司马迁的这种阐释相较于韩非子,对“侠”的高尚节操做了较为具体的要求:即“侠”不仅要拥有高强的本领,更要具备高尚的道德,因为离开了道德的规范,“侠”便会沦落成为胡作非为的“匪类”。因此,自司马迁始,后世对于“侠”的界定便越来越强调其道德要素,从而使“侠”与另一个重要概念相关联,那就是“义”。“义”乃是儒家最为推崇的概念之一,孔子曾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孔子眼中,“义”既是君子的基本的人格,也是君子的崇高品格,并将“义”作为了君子与小人的基本分界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而后世的孟子,更是将“义”这一概念进一步升华,提出了“舍生取义”。据学者研究,自唐人李德裕始———其在《豪侠论》中说道:“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1]95。———“侠”与“义”这两个概念便从此捆绑在了一起,“义”也成为了“侠”的价值体系当中最为核心的一环。因此,后世之侠,不论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存在,还是文人墨客笔下的虚构刻画,都会严守义利正邪之分,正所谓“行侠仗义”。易中天先生说:“有了‘义’,也就有了‘侠’。侠就是义的实现。所谓‘行侠仗义’,就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行侠依仗的是义,实现的也是义,所以有侠肝者必有义胆。什么是侠?侠者使也,也就是见义勇为。也就是说,侠,就是使‘义务’(正义的担当)变成‘义举’(正义的行为)的精神,以及具有这种精神的人”[2]264。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为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侠”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侠”即是有着高超的本领和高尚的人格,以个人的意志和力量来反抗社会黑暗,为此不惜挑战社会既有的法律秩序以匡扶社会道义,并以此为己任的人!
二、“侠”与“法”的对立
从上述“侠”的特质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侠”与“法”似乎是一对矛盾体,其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与冲突(所谓“侠以武犯禁”)。我们不难发现:侠意识,是不承认有法律存在的,他们只会按个人的天理人情来行事,正所谓“替天行道”而非“替天执法”。也就是说,侠的心中只有道义,而无法律,他们当然也不会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他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乃是“义”。因此,我们常说“侠”乃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而至于这一“吼”和一“出手”是否会触犯到现行法律秩序,却不在侠客的考量范围之内。于是,我们就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侠”要替天行道、抱打不平大多是要触犯法律的。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水浒传》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鲁提辖作为“侠”的一个典型,在面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之时,凭借自己的勇气和侠义心肠,毫不迟疑地迎了上去。他为营救弱女子金翠莲而三拳打死恶霸镇关西是弘扬社会正气的正义行为,但却触犯了当时的法律,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被官府通缉捉拿,最终鲁提辖为了躲避法律的追查,不得不委曲求全落发为僧。可见,对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侠义”行为,当时法律给出了否定性评价———鲁提辖乃是大宋律法之下的“要犯”,必须予以严惩。然而,与法律给出的否定性评价相对应的是,千百年来,民间社会却从没有将鲁提辖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来看待,而是将其视为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对之称赞有加。明代思想家李贽就曾在《水浒传》“拳打镇关西”这段文字之后,对鲁提辖给出了“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的高度评价[3]。“仁人、智人、勇人、圣人”乃是儒家理想人格,“神人”是道家的理想人格,“菩萨、罗汉、佛”是佛家的理想人格,因此,中国传统三教“儒释道”的最高称谓,李贽都毫不吝惜地送给了鲁提辖,足见其对鲁提辖的推崇与赞赏。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像鲁提辖这样一个触犯律法的戴罪之人,却为何能够得到民间社会的千古传诵?在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之时,我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为何没有普遍理性地选择运用“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而是去期待游走于法律之外,自掌生杀予夺的“侠”者?笔者认为,在“侠”与“法”这对看似矛盾的概念背后,在民间社会与官方秩序对“侠”这一现象做出的对立性评价的表象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三、民间社会颂扬“侠”之制度根源
众所周知,法律乃是保障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正义的核心力量。因此试想,一个社会如果有着一整套制定精良的法律体系,并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那么,法律本身就足以建构良善的社会秩序,根本无需“侠”的存在,人们也不会在内心中渴望并呼唤“侠”的出现。然而,“良法善治”却是要以一整套能使公权力受到制约并依法运行的政治制度为保障的,依现代政治学的视角来看,这便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为了终止伴随自然状态而在的混乱与无序,人们需要缔结一项契约,并让渡自己一定的权利而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即国家,但人们在建立政权时仍然保留着他们在前政治阶段的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权利。他指出,由人们构成的社会或由人们成立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对不能超越公益的范围,如果它专断地不适当地处理人民的生命与财产,那么它就违反了社会契约的基本条件和它得以掌握权力所依凭的委托关系[4]59-60。因此,在现代民主政治(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民主共和制)之下,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公“权力”也要时刻接受来自于人民“权利”的监督和制约。由此,公权力很难异化成为与人民相对立的“利维坦”,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不会偏离基本的正义轨道。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实行的乃是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一政治逻辑中,公权力的合法性并非源自“民选”,而是所谓的“天授”———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即自称“天子”,人民在官员的选任和升迁中,也不存在任何的话语权。因此,封建时代公“权力”也绝不会受到来自人民“权利”的制约,官员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只是单纯的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封建时代如“州牧”这样的官职名称,似乎更能精准地昭示中国传统社会官员与人民之间的真实关系,即有如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曾经说过:“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4]63。”因此,在失去了来自人民权利的制约之后,封建君主专制下的绝对权力很容易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滋生出绝对腐败,从而在立法与执法两个层面完全背离“良法善治”的正常轨道。首先,从立法层面上看,封建时代可谓是“恶法”频出。例如秦朝的苛法就公然规定:“诽谤者诛,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即敢于公然诽谤朝廷、诋毁皇帝的人,就会遭受灭族的惩罚,而对于那些即便没有公然诽谤、只是私下议论朝廷之人,也会惨遭杀头之祸。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实际上就是在“作恶”。所以“恶法”的存在使得统治者可以在“执行国家法律”的幌子下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这就造成了社会正义的严重缺失,孔子就曾在泰山脚下无奈地感叹“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敢于对抗恶法的“侠”的出现,其形象就显得格外光彩照人。正如前文所述,侠的心中是不承认有法律存在的(何况是恶法),在侠的心中只有道德与正义观念;侠也不会用法律作为他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当然也不会理会统治者在作恶时是在执法还是在违法,只要路见不平,侠客们就会挺身而出、拔刀相助。这样不畏强暴匡扶正义之人,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民间的颂扬!其次,从执法层面上看,文明、公正的执法乃是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而这又依赖于公权力的依法运行。在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社会中,公权力受到来自人民“权利”和公“权力”的双重制约,因此其运行便会在法律规则的框架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君主专制政体中,失去了人民“权利”和公“权力”的双重制约,公权力的运行往往就会挣脱法律的枷锁。于是,徇私枉法、滥用权力的情形就会时有发生。正如阿克顿爵士的名言:“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使人腐化。[5]”因此,在传统中国,在公权力排除制约而逐步异化之后,底层百姓就不免会受到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欺压而无法在既有体制内通过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七剑十三侠》第一回就称贪官污吏、势恶土豪、假仁假义等三种人为“王法治他不得”的“极恶之人”[1]9。因此,在既有的体制和秩序框架内,人民无法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情形下,就必然会寄希望于体制之外力量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而这一力量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足够强大,可以对抗既有体制和官方秩序;其二:秉持正义,可以惩恶扬善,主持公道。而“侠”则恰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第一,“侠”的本领高强,因此力量足够强大;第二,“侠”的心中有“义”,因此会匡扶正义。所以,易中天先生才会相对于流氓“恶霸”而言,将“侠”形象地称之为“善霸”[2]249。明代涨潮曾言:“胸中有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能自掌正义,平天下之不平,那当然最好;至于无此本领的人,焉能不怀念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正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正义的强烈愿望,才不会因为朝代的更替或社会形态的转变而失去魅力”[1]9。所以,司马迁认为,像汉代朱家、剧孟、郭解这样的大侠,信守然诺,舍己助人,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而且功成身退,不求回报,“虽然其行为不符合正统观念(其行为虽不轨于正义),也常常触犯王法(时扦当世之文罔),但个人品质无可挑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享有盛誉是名副其实(名不虚立),受人拥戴也是理所当然(士不虚附)”[2]252。所以,“要使法律成为社会正义的力量,不但法律本身必须公正,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执行必须超越种族、集团、党派的利益。…否则,将给人以一种印象:法律只是某些人的掌中玩物,法律完全丧失了它的庄严”[6]20。如果法律在制定或执行层面就是不公正的,就会出现“有些执法者对侵犯人权的事麻木不仁,然而同时对忍无可忍条件下自行执法的事的反应却出奇地灵敏和严厉,为了垄断权力不惜做恶势力的包庇者”[6]21这一现象。因此可以说,传统中国专制政体之下的公权力异化,以致法律在制定与执行层面出现的不公不义,乃是民间社会对“侠”这一群体赞颂之根源所在。
四、官方体制贬抑“侠”之制度根源
与民间社会对“侠”的赞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对于“侠”均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乃至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侠”的镇压始于何时已无从考察,但可以肯定不晚于韩非子时代。韩非子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贵族,他选择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进而极力反对侠。韩非子在其文章《五蠹》中明确表达了对侠的否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可见,在韩非子的眼中,“儒”和“侠”这两大群体均属社会的负面力量。“儒”整日写文章针砭时政、抨击朝廷;而“侠”则是直接凭借自己力量(以武)将法律取而代之(犯禁),自行主持社会秩序。所以在韩非子看来,“儒”与“侠”这两大群体均是社会的蠹虫,应该大力镇压。而后世之班固,更是在《汉书·游侠列传》中,对“侠”做出了“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罪已不容于诛矣”的评价。因此,我们不禁会问,既然“侠”致力于追求完善的人格与高尚的品德,其所维护的乃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此“义士”、如此“义举”,为何还会遭到统治者的否定?“以德治国”不正是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大力弘扬的吗?这当然不错,但问题的根源却在于:“侠”是民不是官,他们属于传统社会中的被统治阶级而不是统治阶级。因此“侠”绝非“以德治国”的主体,统治者也绝不会允许其成为“以德治国”的主体。事实上,反观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还有一个群体与“侠”同样受民间社会的喜爱与尊敬,千百年来也是不断歌颂称赞———“清官”。我们常常提到的包青天(包拯),海青天(海瑞),于青天(于成龙)等就属于这一群体,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与“侠”也看似相同———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但可见的是,与“侠”相比,统治者对清官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虽亦有时对清官存在着诸多不满,但基本都会将其树立为官吏的榜样,进而加以褒奖———其原因就在于侠客仗剑行侠属于个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他们的功名业绩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国家;而清官为百姓伸张正义则属于政府行为,他们的功名业绩不仅属于他们自己更属于整个国家。清官替百姓伸冤昭雪,百姓们会夸赞政府,夸赞朝廷有道。而侠客行侠仗义替百姓出头,百姓们会夸赞侠客,指责朝廷无道,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更是统治者所不允许的。所以,在统治者眼里,“伸张正义”的事情只能由政府去做,侠客再有道德,也不许越俎代庖。“其实,侠客不讨皇帝喜欢,恰恰就因为他们讲道德,有人格。我们知道,道德与人格是有凝聚力的,比如‘以德服人’,‘以柔怀远’。但我们要记住,在帝国时代,这种凝聚力只能属于王朝,属于皇上,而不能属于其他任何人,任何集团”[2]252。正是在种政治考量之下,传统中国的统治者对“侠”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打击。有学者认为,西汉时期,被汉武帝杀掉的郭解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真实的“大侠”。郭解之后,“侠”这一群体便成了一股松散且不成气候的社会力量———自《后汉书》始,正史便不再为“侠”者著述立传———“侠”也随之成为了中国文人心中的“千古一梦”[2]254-255。然而,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却不应过分怀念“侠”,因为究其根本,“侠”———无论其“义举”如何正当———毕竟是一股游走在国家法律秩序之外的社会力量。因此,一个极力呼唤渴望“侠”的时代,一定是社会腐败黑暗而人民又无能为力的时代。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易中天.帝国的惆怅[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
[3]鲍鹏山.鲍鹏山新说水浒[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87.
[4]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5]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13.
[6]茅于轼.通向富裕和公平之路[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
作者:才圣
- 上一篇:信息技术与政治学科教学的融合范文
- 下一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探究范文
扩展阅读
- 1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 2政治处思想政治总结
- 3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中的应用
- 4时事政治融入政治课堂
- 5思想政治途径
- 6思想政治
- 7思想政治
- 8医院思想政治
- 9生态政治生态化
- 10思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