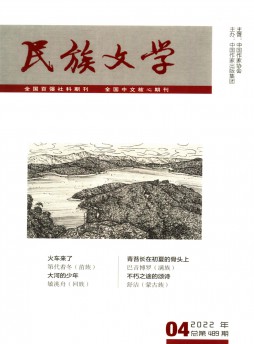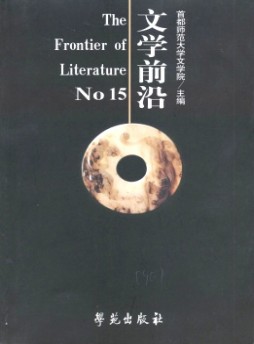文学形象演变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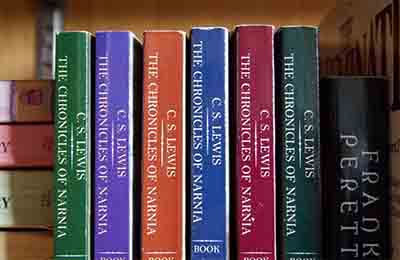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中,涉及日本军人的文学数不胜数。中国当代作家对“日本军人”的描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以前,这时期的“日本军人”形象大都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政治化的倾向,被简单分为“鬼子”和“反战士兵”两极。第二阶段为80年代以来,这时期对“日本军人”的描写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惯性,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学化。概念化向人性化,公式化向深度化的转轨。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日本军人”形象;演变
中国当代文学中,涉及日本军人的文学数不胜数。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日本军人”形象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出现过系统梳理和反思的文。有鉴于此,本文拟结合各个年代的文化、政治语境,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日本军人”形象作出系统梳理,了解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从文学的角度对那场战争以及中日关系做一个理性的反思。
一
中国当代文学中“日本军人”形象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中的日本军人形象集中出现在描写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如《敌后武工队》《风云初记》《平原烈火》《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地雷阵》《敌后日记》《敌后三年》《不屈的昆仑山》《龙山游击队》《苦菜花》《浅野三郎》等。这些“日本军人”形象大都带有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化的倾向。或是狡猾凶残,不堪一击,被中国人轻而易举的获得了胜利;或是忠厚善良,深受日本军国的压迫,在中国人的感召下,成为坚定的反战同盟战士。这种描写既有别于历史事实,也无法解释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
(一)“鬼子”形象
“鬼”是古人对外族的称呼,本来是用来区别夷夏的。近代以来,来中国的外国人多了,“鬼子”逐渐成为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谓。开始时,“鬼子”称谓并不含贬义,它开始于广州,广东人把夜以继日地做生意的英国人叫做“鬼子”,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在晚上活动。但随着外国侵略者的入侵,“鬼子”一词逐渐有了贬义,成了妖魔鬼怪的代名词,如“洋鬼子”、“红毛鬼子”等。尤其是日本战争的爆发,“鬼子”逐渐成为对日本士兵的专用套话。套话是一个民族对异族进行描述时,在民族心理定势推动下一种不由分说的表述,标志着对“他者”的凝固看法。它一方面表现了日本士兵的凶残面目,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人对日本士兵既恨又怕的心理。与“鬼子”称呼相对应,建国后出现了不少对日本士兵暴行进行描写的作品。这类作品中的鬼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日本士兵群体性的描写,即将日军作为一种群体加以表现,表现日军在中国的暴行。另一类是对日本军官的个体描写,这些日本军官身上无不带着几种“滞定型”的特征:凶残、狡诈、好色、愚昧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滞定型”特征却很少出现在作为个体描写的普通士兵身上(不包括作为群体角色描写的日本士兵)。
作为群体描写的日本士兵,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多被写成面目狰狞、杀人如麻的魔鬼野兽形象。如下面的描写很具有代表性:“残暴的敌人如同饿狼扑食未获,越发穷凶极恶。到一庄烧一庄。烧得浓烟遍野,遮住了冬天的太阳,没跑出的病人和老人、孩子,都被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成灰,凄厉的惨叫声,震撼着天地。”…这些日本军人都是以披着人皮的野兽出现的。他们从相貌、性格到行为逻辑,无不体现出兽性,是青面獠牙,杀人不怕血腥的恶魔。二是多被描写成胆小、怕死的愚昧形象。如《龙山游击队》中写鬼子碰到地雷,“吓得爬成一片,连狐狸太君也吓得钻到洋马肚子下面了,好一阵工夫才出来。”《不屈的昆仑山》中描写鬼子被八路军打得溃不成军,“鬼子们抬着尸体,搀着伤兵,一路上,叫爹唤娘,一派狼狈相”。这些描写带着讽刺调侃,具有潜在的娱乐消遣功能,这时的日本士兵,实际上成了中国大众的消遣对象。
对日军群体暴行的描写虽然生动真实,然而却是外部事件的描述。而且大部分作品对暴行的描写模式化,渐渐流于空疏、千篇一律。这是因为作家不能对侵华日军做具体个别的深入描写,不能发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所以难以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个体形象。而将日军描写成怕死的弱虫,实际上是违背了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描写虽然烘托了中国军人坚定、勇敢的高大形象,一定程度地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但却一定程度的误导了读者对日本军人真实、深刻的认识。
为了改变对日军的一般化描写的弊病,很多作家在作品中也尝试着对日本军人(主要是日本军官)做个体描写。但毕竟中国作家不是日本人,他们很难体验日本军人的杀人心理,对于他们野兽般的行为也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只能将他们现在听到的、或以前见到的情景,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进行描写。再加上中国意识形态很浓的文艺理论的指导,这样就很容易将日本军官描写成模式化、脸谱化的“滞定型”形象。概括起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军官大致有这样几种“滞定型”:凶残、好色、伪善。
“凶残”是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军官最典型的特征,《新儿女英雄传》中的岗村指挥他的狼狗去咬中国人,“一直到狼狗舔着嘴角的血,用血红的眼睛望望梁上那个中国人已经变成一副骨头架子”;《苦菜花》中庞文大队长用酷刑折磨着七岁的小孩,“皮鞭在孩子赤露的幼嫩身上抽打,一鞭带起一道血花!……”与日本军人种种凶残行为相对应,中国作家在描写上也渐渐将他们野兽化。对日本军人的外貌描写中,常常用到的词语有:“疯狗似的”、“黄呢子野兽”、“毒蛇一般”、“恶狼”等。
在中国作家笔下,日本军人都很“好色”,见到女人就要进行奸污,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甚至是怀了孕的女人。《龙山游击队》中的狐狸太君见到女人就用他“那双淫秽的小三角眼,死死盯在人身上”,被他奸污的中国女人不计其数。《苦菜花》中庞文大队长最大嗜好就是“玩女人,有一次找不到年轻的,抓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他也不放过”。
“伪善”也是日本军官常见的特征。笑脸下面隐藏的是凶残的面目,体现出了日本人狡猾的一面。《铁道游击队》中鬼子为了从小孩嘴里套出游击队的消息,分糖果给小孩吃。《新儿女英雄传》中的松尾见到中国人常常“装出和气,脸上老不离笑容,爱讲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并握着对方的手笑着说:‘我喜欢和中国人交朋友!’……可他杀人却是厉害,而且都是在夜间秘密的处决……”。
总的看来,这阶段中国作家在表现日本“鬼子”形象问题上,具有几个鲜明的特点。(1)几乎所有的“鬼子”最后都遭到了失败、惩罚或击毙。如果说文学作品机制就是在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叙事情境中,通过对生活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想象性的解决,把广大读者编织于一个文化经验的幻想之中。那么,中国这个阶段的文学正是通过对“鬼子”的最后惩处,完成了安抚中国人民倍受外国列强侮辱和欺凌的心灵,并唤起民族自信心的文化功能。(2)几乎所有的“鬼子”都是配角。这一方面与中国当时的文艺政策有关,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要求作家将英勇无畏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连“中间人物”都不能做主人公,更何况是罪恶满贯的“鬼子”。他们只能作为英勇无畏的中国人的衬托而出现。另一方面,这实际上也是创作者对日本军人存在“刻板成见”的一个典型表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所犯下的罪行是记忆犹新的,这些在作品中作为配角的“鬼子”形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根据自己对鬼子的理解和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而不是作家深入进行生活实践而创作出的人物,自然就不可能达到做主角的要求。(3)单个的、滞定型的鬼子形象一般以日本军官为多,日本士兵被描写成鬼子形象时,多作为群体描写,单个描写的很少,这无疑与中国作家对日本士兵所做的阶级分析有关。在中国作家眼中,日本士兵与日本军官是属于不同的阶级,具体描写坏人形象时,只能描写日本军官,而作为群体描写的日本士兵所做的恶事是受日本军官欺骗的,他们是可以被转化的。
(二)反战士兵形象
与凶残的“鬼子”形象相对立的,是作家们塑造出来的日本反战士兵形象。日本反战士兵是指反对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士兵。在抗日战争中是否有这样的士兵,答案应该是:有,但却是很少很少。中国人坚持这样的看法:日本士兵是日本老百姓,是受日本军阀欺骗来中作战的,他们在侵华战场上丧失人性的行为是军国主义毒害的结果。因此,这些士兵经过一定的教育和感化,是可以恢复人性,甚至可以走到反战立场上来。这些日本士兵形象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无产阶级出身的普通士兵,这与单个“鬼子”形象都是日本军官形成了对应。如《浅野三郎》中的浅野出身农民,《哗变的“皇军”》中的井上、木村等出身渔民等,他们都是在日本军部的强迫下来到中国参加侵略战争。在日本军队中,他们受到了日本军官凶残的对待,渐渐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他们或是在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接受了中国军队的教育,或是在同胞的反战同盟的宣传中渐渐认清了这场战争的真实面目,“日本的老百姓和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是在“替那些靠战争发财的大资本家去打战,是在当法西斯的炮灰”,而“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军阀和财阀,对于日本军队的士兵,是讲国际主义的”,在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这些日本士兵积极投身于中国反战运动,有的甚而为中国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浅野三郎》中的浅野,《哗变的“皇军”》中的岩崎。有些反战士兵甚至被塑造成类似于中国共产党员形象,《哗变的“皇军”》中的岩崎,他机智、勇敢,帮助战友逃离军官的摧残,向士兵宣传反战思想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最后领导战友集体投向新四军,从头到尾俨然是个中国共产党员形象。而且这些反战士兵形象许多不再是配角,而成为作家笔下的主角。
中国作家塑造的这些日本士兵的形象,显然采取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立场,对日本士兵的定位和分析所采用的也是中国左翼文学常用的阶级分析方法。由于这样的立场和方法,《浅野三郎》《哗变的“皇军”》之类的作品,就带上了一定程度主观化、概念化和理想化色彩。日本士兵的这种形象与实际形象相差很远,即使有这样的日本士兵,那也是极为少数,缺乏普遍性和典型性。这些作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作家对日本军人以“忠君爱国”为核心,以“义理”、“荣誉”、“廉耻”、“复仇”、不成功便成仁的“自杀”、绝对服从主人和上司等武士道精神为基本内容的日本民族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实际上,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士兵都是日本普通老百姓,而他们在中国所做的一切罪恶,并非都是日本军阀逼着干的。他们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地达到了和法西斯军阀的一致,非常容易地、自觉地毁灭人性,这才是他们的可怕之处。而善良的中国作家一厢情愿的将他们与日本军阀机械的加以区分,从而塑造出一系列正直、善良的日本士兵形象,不能不说是有违历史的。
通过上面对8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日本军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鬼子形象也好,反战士兵形象也好,实际上都担负着非常复杂的功能和“任务”:宣泄、抚慰中国人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心理,反衬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勇敢智慧为主要内容的优秀民族精神,突出中日无产阶级是一家的思想,担当中日人民友谊的桥梁等等。二
新时期,中国抗日文学开始了历史性的转轨。从“”结束到80年代中期,是抗日文学的前突破期,虽然也有《最后一幅肖像》等探索性文学出现,但大多是一种悄悄的变化,不很明显。到80年代中期,随着《长城万里图》(周而复)《新战争与和平》(李尔重)等长篇小说,《红高粱》(莫言)和《黑太阳》《酋长营》《支那河》(张廷竹)以及《军歌》《大捷》(周梅森)等中篇小说的出现,抗日文学开始进入了后突破期,摆脱了传统文化的惯性,走上了由政治化向文学化、人性化的转轨。
新时期对日本军人形象的塑造,与前一阶段有延承。“鬼子”形象仍很多,如《红高粱》中的活剥人皮,《生命信道》中用中国人做活体解剖,《漠野烟尘》《白太阳红太阳》中用中国人作练胆的活靶子,《天镇老女人》《风》中无数中国男人被侵略者残忍地割下生殖器,为的是让中华民族种族灭绝。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角度来说,一味地魔鬼化和野兽化日本鬼子,只能增进中国年轻一代的复仇意识,无益于睦邻友好,不利于文化交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鬼子的恶魔形象一再被重复描述,而且愈演愈烈,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日本右翼军国势力死灰复燃的警惕,这是日本在经济上重新崛起后,一系列对外政策所导致的“恐日症”的必然结果。同时,“反战士兵”也不断出现,《弹痕》中坂村六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人打鬼子,《长河落日》中的绿川英子向日本军队进行反战广播。但更多的是突破,新时期的作家开始把战争中的人以及特殊境遇下人的心灵世界作为其艺术表现和关注的中心,并且开始准确、公正地勾勒出日本人的外在形象,透视出这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这对于我们了解过去的日本人,观察今天的日本人进而把握他们明天的精神走向,是不无裨益的。
首先,新时期的作家打破了日本士兵与日本军官的阶级分界线。来自下层的日本士兵不再只是被日本军阀欺骗来打战的良心未泯日本老百姓,他们同样也是我们战场上可怕的敌人和对手。如尤凤伟的《生存》中的日本士兵小山做了俘虏还不服软,一个劲地和中国人作对,使出种种诡计对付中国人,最后和中国人同归于尽。邓贤的《大国之魂》中的护旗兵田忠一郎“好像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高挚手榴弹从死人堆里站起来”,“扑向正在开会的中国人,尽管担任警戒的中国士兵及时掉转抢口,这个日本人还是奋不顾身地拉响了手榴弹”。当美国海军战斗机攻击日本海军总司令三本五十六乘坐的轰炸机时,“红着眼睛的日本战斗机飞行员一个个奋不顾身,英勇地扑向美国飞机,试图保卫自己的总司令”。正是这些来自普通民众的士兵组成了这支可怕的军队。
而日本军官也并非全来自剥削阶级,如纪实作品《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号人物——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来自于工人家庭,邓贤的《日落东方》中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是一个渔民儿子。日本军官也不再是被描绘成固定的丑恶凶残形象。陈道阔的《长河落日》中冈村中将“白净的面皮和清秀的眉目透出儒将的飘逸风度”。《大国之魂》中的日本师团长松山佑三有着清秀、坚毅的面容,面对“怒江东岸的敌人十倍于他的士兵,他丝毫也不感到胆怯或者悲观。因为他需要加以证明的正是这一点:日本皇军不仅能够以一当十,而且最终还将征服全世界。”这就是日本军官的战争气质。
其次,作家开始认真思考日本的民族精神,思考日本军人胜利和失败的内在根源。《大国之魂》中写到日本士兵在战场上的表现:“日本人的确非常顽固,往往堡上层烧坍了,下层继续往外打枪,直到烧死或者把地堡彻底炸坍为止,总之没有人投降。后来一直达到松山主峰,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还没有捉到一个日本俘虏。”“听说日本人手榴弹打光了,就扛起迫击炮往石头上砸”。“亮剑”中山本大佐“嗜血的渴望,战斗的激情使他几乎欢快起来,一套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已经在脑子里迅速形成。”《生存》中日本俘虏死不投降,他们坚守着他们的信念:“大日本皇军性命是属于天皇的,生为天皇征战疆场,死为天皇捐躯尽忠”。
如果按照人的意愿去组建一支最优秀的军队,那么它的成员们似乎应该具备以下的素质:怀有坚定的信仰和对国家、民族的绝对的忠诚,勇猛残酷,守纪律,同时又有文化、懂技术。当我们用上述指标衡量日本人的时候,不难发现;整个日本民族就是一支最理想的军队,每个日本国民都是最优秀的战士。这支最优秀的军队,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军队。他们具有“武士文化的羊与狼,严谨的修身与疯狂的发泄的双重人格”。这种菊与刀并存的民族精神,是日本军人胜利和失败的内在根源。战争机器一开,日本几乎所有的人,“也就是被称为‘人民’的绝大多数日本国民都被动员起来,自觉自愿地、主动地、亢奋地、不可遏制地投入到侵略和屠杀另一个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人民的‘圣战’中去”。这种可怕的精神不仅表现在军人身上,日本普通百姓也表现出狂热和盲从的一面。《花之殇》中绢子自愿作军妓,因为她认为“日本女人也应该向日本男人一样,为天皇建立奇勋”。胜子作军妓,竟时受了未婚夫的感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天皇陛下的。当前,全体日本国民都要为大东亚圣战贡献自己的一切,我希望你在本土,也不要忘了你作为日本国民的责任,一旦需要,哪怕是你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不管我们感情上接受与否,日本兵蜂窝一样身捆手榴弹拥向苏军坦克,成群的战机撞向美驱逐舰,听到天皇投降后的集体自杀殉国。这种令人不寒而栗的作战方式让人在震惊之余难免要生出一些钦佩之情——为了一种事业(当然这种事业是非正义的)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与日俘中鲜有投降者相反,中国虽然也有“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但中国人确是出了大批的汉奸翻译,出卖同胞的内奸,为虎作伥的伪军,甚至在日军的刺刀威胁下活剥同胞者(《红高粱》)……与日本鬼子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相比,中国这么多的“好死不如赖活”者是否与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有关?作家们通过他们的笔锋透视日本人外在行为方式,自然地指向了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住了日本人的精神脉搏,同时也用批判的眼光发现了我们民族中的某些劣根性。
第三,新时期以来的抗日文学,从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战争与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即使是对日本侵略者,也从人性视点上进行了客观和真实的描写。1989年,《芒种》第2期发表了陈放的短篇小说《最后一幅肖像》,揭开了探索侵略者人性问题的序幕。故事中一位日本军官崇拜美和艺术,当他认定的一个优秀的中国画家死于自己的枪口之下时,表现出了痛惜之情。这篇小说在艺术上并无特别突出的价值。但由于它反映了特定条件下,侵略者一息尚存的人性,使人们认识到,敌人也是人,也有爱美之心,恻隐之心,改变了以往观念中的固定模式,使抗日小说在人的理解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叶兆言的《日本鬼子来了》更大胆地把侵略者推向了普通人的形象行列。小说中的三良,是个40多岁的老兵,家中有妻子儿女。一次他闯进阿庆嫂家强奸了阿庆嫂,但不知何种原因,他竟喜欢上了她,以后便不断地来。“作为日本鬼子的三良,在大家印象中已经离万恶不赦的恶魔有很大距离。”“农忙里,他还屁巅巅地跑去帮忙……一头一脸地泥,看看都好笑。”《生命信道》中的高田军医队长一方面参与日军枪杀中国人的行动,另一方面又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中国人,体现了人格的两面性和矛盾性。《虎贲》中在一名死去的日本少佐“上衣口袋里有一块怀表和一张照片,照片是一个是日本女人及两个日本小孩的合影,大概是他的老婆孩子”。岳恒寿的《跪乳》中几个丧失了理性的日本兵在伟大的母爱面前,唤回了他们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
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审视和表现侵略者,第二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以人道主义精神,去理解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普通日本人的命运。新时期以来的抗日文学,在人的意义上,对战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比如在战争中,有大约一万名日本儿童遗弃在中国,这些孤儿的人生遭遇,直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成为中日间共同关注的问题,才进入一些作家的创作视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女作家叶广芩的长篇纪实小说《战争孤儿》,书中这些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孤儿,尽管身上流淌着日本民族的血液,却是在中国的大地上长大的,他们已经难以改变地有了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因此,当他们回到日本以后,便产生了一系列的精神危机。有的在绝望中自杀,有的被推到了死亡极端,有的将自己灵与肉的爱心迅速销蚀在异化的社会里。再如《殇》、《花之殇》《无往地带》等描写了日本女性在战争中沦为军妓的悲惨命运。这些来自日本本土的慰安妇,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日本军人,却时常遭受自己同胞“婊子”的臭骂和性虐待,在日军面临彻底灭亡时,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有意义的生存变成了无意义的死亡,即使发生在敌人一方,从人的立场上看,仍然是不幸的,值得同情的。小说在对他们不幸命运同情时,同时也对战争发出了来自内心的诅咒。
第四,作家开始描写日本军人在战后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态度,开始对这场用无数中国人血和肉堆砌成的战争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战争孤儿》中的吉岗龙造,一个过去的侵华日军,不仅至今仍珍藏着他在中国拍的杀人的照片和战刀,而且一谈起他战时杀人的情景,禁不住兴奋不已:“站在背后,瞅准第七颈椎的位置,落手要迅猛,进刀与锁骨呈17度角,几乎不费什么劲儿,头颅就横推下来了,游刃有余,连骨喳儿也没有,干净漂亮……”肖平的《归来》中一个滞留中国30余年的日本妇女夏子回到日本探亲,但她发现哥哥等旧军人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军国主义思想,他和他的“占有会”的人对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不仅不忏悔,反而辩解说,“战争就是这样,失败的一方没有资格说话了,对方就编造出许多坏事安在他们头上。这真叫人生气。”这些难道不让人震惊吗?《大国之魂》中作者在后记描写道:“改革开放,杀人魔王又回来了。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民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据说日本天皇设有,麻脸军曹也没有。”作者的字里行间蕴涵着对这些日本人的愤怒,他从这个杀人魔王身上觉察到了日本人的优越感,认为这样的民族是不容易汲取教训的。昔日的妖魔还原为真实的人,读后令人战栗:日本人身上有极可怕、极厉害的一面。这就是日本人对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罪行的反思。他们不仅不忘他们所谓的“圣战”,而且不承认他们的战争罪行。这样的民族,怎么不值得深受战争伤害的中国人民警惕?
而提高警惕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忘记历史。灾难的制造者还时时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作为战争受害者,却正在忘却历史。张华亭的小说《葬海》以一个老人悲愤的呐喊,向人们敲起了不要忘记历史的警钟。在渤海湾的一个方圆不足半里的海湾,是当年日本军队挖出来的。在这个海湾里,曾经发生过一次血腥的屠杀。那些侵华日军“将刀架在孩子、大人的脖子上,互相比赛着往海湾里削,看谁削得远,削在海湾的正中……”。老人的父亲、母亲、妻子统统死于这场劫难。然而他唯一的孙子靠在海湾里捞海参发了财,在酒醉后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日本人好啊,亏了日本人挖这大湾……”老人结尾时的呼吁“都来恨魔鬼吧!都来记住魔鬼留下地罪恶……”让人感到沉重与压抑。中国人真地这么健忘吗?这健忘的背后,是我们民族宽大胸怀的表现,还是民族忧患意识的缺乏?
公平的说,许多日本人都是善良、爱好和平的。我们也常见到日本人来中国后对他们民族在过去犯下的罪行忏悔,但也的确有许多日本人包括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对日本军队所犯下的罪行讳莫如深,用各种理由开脱罪责。这些人无视历史事实的卑劣态度,严重的刺伤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新时期的作家们通过描写这些日本军人形象,更好的提醒中国人去思考:日本民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这种悲剧以后还会不会再发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每个中国人去深思的。
精品推荐
- 1文学与文化论文
- 2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 3文学专业论文
- 4文学价值论文
- 5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 6文学作品分析论文
- 7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利与弊
- 8文学作品论文
- 9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 10文学写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