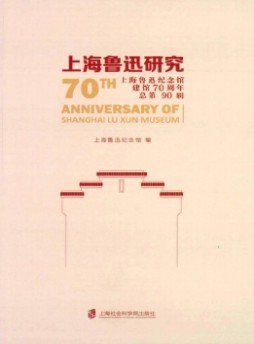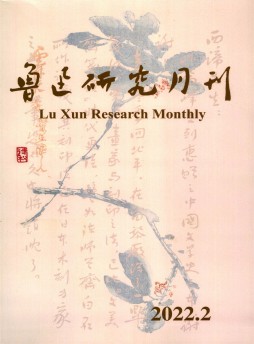鲁迅基本走向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一方面各国之间的诸多壁垒逐渐被拆除,这使得鲁迅作品在世界上的传播渠道更为畅通;另一方面,苏联、东欧国家原先因意识形态缘由而形成的对鲁迅的特殊兴趣不复存在,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进入低谷。同样也是因为冷战的结束,鲁迅在亚、非、拉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日益缩小。但是在日本等远东国家和北美、西欧及其澳洲国家,研究鲁迅作品的学术条件进一步优化,鲁迅在这些国家的传布出现了新的特点。本文将对20世纪90年代以降北美、澳洲和西欧①的鲁迅研究状况作初步的介绍和评价。
美国学者本时期发表了大量阐释鲁迅思想和作品的论文,这些论文有的是登载在学术刊物上,有的是被收录在论文集里。在90年代初,黄维宗(音译)的论文《无法逃避的困境:〈阿Q正传〉的叙述者和他的话语》,对《阿Q正传》所作的叙事学分析,显示了运用结构主义方法论阐释文本的可行性。杨书慧(音译)的《道德失败的恐惧:鲁迅小说的互文本解读》,借助西方新的阅读理论,在鲁迅作品之间建立起“互文”关系,使它们成为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鲁迅研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华裔学者的鲁迅研究成绩相当突出,老一辈学者林毓生继续关注鲁迅思想的矛盾性,他的论文《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含义——兼论“国民性”问题》从鲁迅1925年5月30日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谈起。在这封信中,鲁迅说自己的思想有许多矛盾,“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在他身上“消长起伏”着。林毓生动用自己治思想史出身的知识储备,证明在西方思想史上,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无冲突,相反倒是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两种“主义”在鲁迅身上会发生冲突呢?经过考证,林毓生发现《两地书》铅印本对原信作了删改,鲁迅在原信中说的是“人道主义”与“个人无治主义”的冲突,“个人无治主义”即是无政府主义,与“个人主义”差别很大。那么鲁迅为什么在信件出版时要作改动呢?林毓生分析道,鲁迅“一方面有‘安那其个人主义’的冲动,另一方面又觉得那是不负责任的‘毁灭’之路;一方面他仍不能不受人道主义的感动,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没有条件的‘大爱主义’在现实世界上行不通,在这种思想困境中,难免顺着自己写文章的习惯做一点修辞上的工作了”。
接着,林毓生在论文中开始讨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问题,他认为鲁迅在此问题上走向了“逻辑的死结”。首先,“国民性”分析范畴具有很强的决定论倾向:假如中国的一切都是由国民性决定,那么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其本质是不会变的;其次,国民性到底是中国问题的原因还是后果也说不清楚。于是难免就走向逻辑死胡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认清重疴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鲁迅思想陷入困境,在日本侵华后,作为爱国者的鲁迅必须采取政治立场,“而中国马列主义已经提出了一套革命的计划与步骤,于是他便在未对它做深切研究之前,成为共产革命的同路人”。林毓生对鲁迅思想困境及其衍变路径的阐释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研究方法比较新颖,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挑战性,值得鲁迅研究者关注。
唐小兵的论文《鲁迅的〈狂人日记〉和中国的现代主义》论述了鲁迅创作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创性贡献。王德威的《鲁迅、沈从文与砍头》探讨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不同的砍头描写方式,以及不同砍头描写方式背后蕴含的道德、美学尺度。王德威认为,鲁迅在砍头场景中看出中国的社会民心和中国的道统象征不可收拾的土崩瓦解;沈从文面对同样的场面,却试图从文字的寓言层次,提供疗伤弥缝的可能。鲁迅在身体断裂、意义流失的黑暗夹缝间,竟然发展出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王德威在论文最后总结道:“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数接受了鲁迅的砍头情结,由文学‘反映’人生,力抒忧国忧民义愤。他们把鲁迅视为新一代文学的头头。沈从文另辟蹊径,把人生‘当作’文学,为他没头的故事找寻可以接上的头。因此,他最吊诡的贡献,是把五四文学第一‘巨头’——鲁迅的言谈叙事法则,一古脑而地砍将下来。他的文采想象,为现代小说另起了一个源头,而他对文学文字寓意的无悔追求,不由得我们不点头。”
王德威写得“头头”是道,的确显示了他恣肆的思辨力,他曾经在林毓生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对该校历史系前辈林毓生的学术理路应该比较熟悉,这两位华裔学者的论著都显示出突出的思辨能力。但他们的学术论著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总是预先设定一个前提(也许他们不愿承认),在林毓生那里是设定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思想家都有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the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approach),由此证明他们的反传统是陷入了困境;在王德威这里是预设鲁迅与沈从文的写作有着质的区别,再根据这一预设去寻找两人的差异。然而,鲁迅与沈从文的思想和创作既显示了差别,又具有共同取向(新加坡大学教授王润华对鲁迅与沈从文共同性有过研究)。总之,王德威就鲁迅和沈从文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见解,但他的论证方法存在着的问题决定了他的观点只能是一家之言。
张隆溪的《作为基督的革命者:鲁迅作品中未确认的拯救者》,是一篇力图在革命话语与基督教话语之间寻找诠释鲁迅创作之可能性的论文,显示了在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话语之外鲁迅研究的阔大空间。梅仪慈的《文本、互文本与鲁迅、郁达夫、王蒙的自我表现》把三位中国现当代作家放在一起,通过他们作品的互文本关系,探讨中国五四以来文学的自我表现倾向。本顿·格瑞格的《鲁迅、托洛斯基以及中国的托洛斯基主义》对学术史上争议不断的鲁迅和托洛斯基文艺思想关联问题作了深入的考察,确认了两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岳刚(音译)的《鲁迅与食人主义》[9]是研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食人主义”批判立场的文章,也展示了鲁迅作品对“吃人”主题的艺术表现。
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鲁迅研究者继续保持着高度的学术热情,写出了不少论文。卡迪斯·尼古拉斯撰写的论文《作为审美观照的散文诗:鲁迅〈野草〉研究》[10]从美学视角探讨了鲁迅《野草》的意蕴和创造力。施书梅(音译)的论文《进化主义与实验主义:鲁迅与陶晶孙》[11],抓住中国思想史的进化主义和实验主义两大线索,对鲁迅和同样曾经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陶晶孙的思想和创作作了比较性的研究。保罗·福斯特撰写的论文《中国国民性的讽刺性膨胀:鲁迅的国际性声誉、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及诺贝尔奖》[12],对围绕着《阿Q正传》在世界上的传播和影响问题进行了论评。《鲁迅小说的反讽和批判现实主义》[13]与《荒诞修辞学:余华与鲁迅创作中的荒谬性》[13]都是出自王班(音译)之手的论文,前一篇从反讽角度研究鲁迅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特征,后一篇在小说修辞学层面上对鲁迅与当代作家余华创作中的荒诞性作了创造性的阐释。
再看专著方面,90年代以来,美国出版了几部专门研究鲁迅的专著,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学术著作也把鲁迅当作重点。寇志明的《诗人鲁迅:鲁迅旧体诗研究》由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印行,将在介绍澳洲鲁迅研究时再作评述。
J.R.普赛的《鲁迅与进化论》[14]分九章,在自中国近代以来进化论的传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鲁迅与进化思想的关系。《鲁迅与进化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踪中国鲁迅研究界如何评价、探讨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学术线索,并不时加入普赛个人的评价。普赛指出,青年鲁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国学者说成是受了达尔文主义及其分支学派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但普赛引用美国著名的严复研究专家本杰明·施瓦兹(BenjaminSchwartz)的观点,认为鲁迅青年时代阅读的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实际上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攻击”。中国学者普遍把鲁迅的思想说成是经历了从进化论到唯物论的演进,普赛反对这样的描述,认为“鲁迅思想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变化”,“真正的鲁迅是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认为鲁迅的思想几乎是不变的观点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内好提出过,关于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阐述。普赛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上述看法并无多大不妥,问题在于普赛把这部专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质疑、批驳中国学者上,多少显露了他精神深处还残留着某种“冷战”思维的痕迹,虽然普赛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战”思维的陷阱的。
玛丽·法夸尔的《中国的儿童文学:从鲁迅到》[15]是一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论专著,它的第二章《鲁迅与儿童世界》研究了1903-1936年间鲁迅关于儿童及其文学的写作情况,主要阐述了四个问题:
一、鲁迅和中国的西方儿童文学翻译;
二、清末鲁迅的早期儿童文学翻译;
三、鲁迅与五四前期的儿童文学;
四、鲁迅与五四后期的儿童文学。在这一章的结论部分,玛丽·法夸尔指出,儿童及其文学的属性一直为鲁迅所关注,但鲁迅的兴趣总是集中在儿童及其文学所预示的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上,鲁迅的这一思路对后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德华·冈的《重写中国:20世纪中国散文的风格与创新》[16]虽然不是鲁迅研究专著,但它对鲁迅的《朝花夕拾》、《野草》以及杂文创作的情调和艺术都作了比较充分的阐释,提出了一些较有见地的看法。
安德森的专著《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17]第三章《鲁迅、叶绍钧与现实主义的道德阻碍》的第一节《鲁迅:观察的暴力》,对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及其道德困窘作了精彩的阐述。安德森举日本教室里的幻灯片事件、小说《示众》的示众场面和《阿Q正传》的“牺牲仪式”为例,就鲁迅作品对“观看”暴力场面的现实主义艺术表现作了深入探讨,他甚至分析出了这样的意味,“在迫害者与受害者的目光碰撞中,暴力的走向被瞬间扭转:无论多么短暂,被看者(被粗暴地选中的示众者)成了看客,而看客(中国庸众,甚至也包括读者自己)成了被看者”,“这一刻,读者体验到,公众的暴力恰恰植根于他们的行为在受害者心中激起的恐惧”。[17]藉此,鲁迅对自己的写作和现实主义的艺术作了强烈的质疑,“他暗示现实主义可能会使作家屈从于他们打算谴责的社会残暴,在形式上描写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间关系的现实主义叙述,有可能会被压迫逻辑俘获,最终只成为压迫的复制”[17]。安德森竟然在现实主义文学对暴力的揭露性展示中,读出了这种艺术表现方式与暴力制造者之间暗含的“同盟关系”,的确是深刻的诛心之论,这也是安德森的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整体思路:艺术形式其实是隐含着道德因素的。安德森的这番研究,就把对文本的艺术分析与内容分析结合起来,使它们成为有机的整体。
华裔学者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18],是一部在海外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震动的专著,她的主要观点是:在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观念在数不尽的翻译、复述中丧失了西方的本原意味,成为“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在该书的第二章《国民性理论质疑》中,刘禾探讨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西方传教士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的关联,认为“国民性”是一个隐含了西方霸权和优越感的话语,认为鲁迅“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18]。刘禾通过分析《阿Q正传》的叙事,认为鲁迅创造了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叙事人,这使得小说超越了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大幅改写了传教士话语”。[18]刘禾大胆提出新见勇气诚然可嘉,但她把国民性问题仅仅当作西方传来的“翻译的国民性”,就比较偏颇了。中国现代国民性理论的确受到了西方的深深影响,但是中国就如英国、法国或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自己的国民性,这也是不能轻易否认的事实;而鲁迅创作中展开的国民性批判乃是植根于中国的本土历史与现实,因此,鲁迅的创作总能够引起多数中国人的共鸣。
1998年华裔学者李天明在加拿大中国学家杜迈可(MichaelS.Duck)的指导下,以《鲁迅散文诗〈野草〉主题研究》的论文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李天明在自己的英文学位论文基础上改写的著作《难以言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在国内出版[19],该书从社会政治批判、人生哲学思考以及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这三个层面,对鲁迅《野草》的主旨和内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发,书后所附《英语世界〈野草〉研究简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与美国、加拿大同属英语世界的澳大利亚在本时期出现了一些学术水准较高的鲁迅研究成果。G·戴维斯的长篇论文《阿Q问题的现代性》[20],考察了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意识形态危机背景下,革命文学论争中钱杏邨、冯乃超等人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批判,并揭示出阿Q终极悲剧的现代性问题。戴维斯认为,小说的“大团圆”诱使“读者去探求阿Q表面‘无意义的’生存背后所隐藏的深刻含义”,正是阿Q“这种‘存在的被抛入性’使读者产生一种热切的愿望:为阿Q的存在赋予意义”。[20]
原籍美国的寇志明(JonKowallis)任教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在90年代推出了一批鲁迅研究成果,他的著作《诗人鲁迅:鲁迅旧体诗研究》[21]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介绍鲁迅生平和文学创作情况的“导言”,主要向一般读者提供鲁迅旧体诗的时代和作者的传记性背景,还就中国五四以来的旧体诗写作,以及鲁迅的创作个性所受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影响等问题作了学术探讨。第二部分是寇志明翻译的、按照编年体排列的鲁迅现存64首旧体诗的英文译本。寇志明的译诗用英语诗歌的音韵来押韵,并使用了英诗的音步(音尺),使译诗尽可能成为格律诗,以传达鲁迅原诗的古典风格。寇志明给每首诗都作了导读,除了解释诗篇的意蕴外,还尽量引用鲁迅的书信、他的文章的序言,以及亲友的回忆中有关的说明文字,为读者理解诗篇提供参考。总之,这是一部有利于英语世界的读者解读鲁迅旧体诗的著作。
寇志明的论文《节日之于鲁迅:“小传统”与国民身份认同建设》[22]指出,鲁迅在《朝花夕拾》、自传性小说以及其他回忆录作品中,围绕他过往的生活创造了一种“梦幻式的氛围”,鲁迅的回忆中通常使用“节日”作为回归过去生活的主要道具,在这些节日描写中,出现了一连串民间神灵和表演人神共庆的戏剧场面。论文考察了鲁迅少年时代的习作《庚子送灶神即事》,以及他后来创作的《送灶日漫笔》、《祝福》、《社戏》、《五猖会》、《无常》等作品中的节日描写。论文的结论是:鲁迅在写节日的时候,“都提供给我们一种多侧面的民国时期对民族国家进行确认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而且也不经意的对后来共产主义定义中国大众文化的意图进行了反思”,“对鲁迅来说,节日的仪式和戏剧更多是作为社会批评的比喻,而不是作为对俗文化在创造‘新’的民族文化中所占地位的肯定”[22]。寇志明还写有《鲁迅与果戈理》[23]这样的比较文学论文,对鲁迅和果戈理的同题小说《狂人日记》的意蕴、人物和艺术诸方面进行对照,比较了鲁迅与他的俄国文学前辈创作的异同。
英国学者的鲁迅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但显示了稳扎稳打的求实精神。波尼·麦克道戈尔和凯姆·劳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24]属于文学史著作,其中对鲁迅的创作有较多的评述。在论及《野草》时,该文学史指出,“这些散文诗融记事、讽刺、怀旧、梦幻和短剧、打油诗等多种风格和技法于一体”,“《野草》在主观性、抒情性风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见的尝试”,“鲁迅对‘黑暗力量’的执迷构成《野草》的基本线索”。[24]该文学史对于鲁迅的小说创作作了更充分的评价,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从灵感和标题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它是中国第一篇同时使用文言和白话写作的小说,序言用文言写作暗示了这种语言的权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读者群需要被启蒙。当然,该文学史也显示了西方学者还未能完全摆脱把鲁迅的小说当作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反映的这一传统的分析模式,比如对《阿Q正传》、《药》等作品的阐释,就基本把它们定位在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上,这恐怕也是受了中国国内学术界庸俗社会学研究模式的影响。
卜立德在上一个时期就撰写了一些鲁迅研究的论文,他70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专著也对鲁迅多有述及,成为英国一位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卜立德自80年代末以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高校翻译系任教,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关于鲁迅的论文就有好几篇。在《〈呐喊〉的骨干体系》一文中,卜立德对初版《呐喊》的十三篇小说进行了解读,试图勾勒这部小说集的基本框架,他认为《不周山》只是神话的改写,《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几篇实际为纪实文章,而《头发的故事》、《端午节》、《白光》很少被人关注。卜立德对《呐喊》其他的小说作了“新批评”式的细读,读出了一些独特的意味,他认为《药》写坟墓的氛围与其说是和安特莱夫的作品接近,不如说更接近法国作家缪塞《世纪儿忏悔录》主人公向天呼唤的一节,从所引的缪塞作品来看,卜立德说的的确有些道理。认为在《孔乙己》中由于叙述者抑制自己的同情态度,反而造成读者对孔乙己的更大同情。认为对于鲁迅笔下那些被人压迫,同时又互相欺骗和苛待的中国人来说,反讽可能是唯一的描写笔法。认为鲁迅的反讽是多样的,“有时沉重,有时挖苦,有时开玩笑,它隐藏着同时又揭示一种爱恨交缠的复杂感情,这给予他的杰作以感情的深度,是至今无人可比的”[25]。
卜立德的《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对鲁迅1903年留日时期尝试翻译的凡尔纳的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文本作了深度研究。鲁迅这些译本是从日文译本转译而来的,而日译本不是直接从法国作家凡尔纳作品翻译,而是从英译本转译。作为从事中西翻译研究的学者,卜立德精通英、法、汉、日等语言,由他来研究鲁迅早期这两篇译文是比较合适的。卜立德从日本国会图书馆找到了凡尔纳这两篇小说的部分日译本,把他们与鲁迅的汉译本对读,发现了很多问题,原来日译本对原著改动很大,鲁迅对日译本也有所改译。卜立德在鲁迅翻译的两篇小说、日译本残卷、法文原著之间作了精细的校读,发现《月界旅行》的日本翻译者对原著任意改编的情况很普遍,鲁迅的译本只是在日译本基础上加以修饰、整理、夸大,但章回体式的回目是鲁迅加上去的。而在《地底旅行》翻译过程中,鲁迅加进去了不少“败笔”,尤其是对小说对话的翻译问题较多,这对原著是一种“破毁”。卜立德是研究中西翻译的行家,他当然知道20世纪初年改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中国知识界的一种风尚,林纾和梁启超随便改译的外国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卜立德对于鲁迅的翻译水平总体评价不很高,但他写这篇论文不是为挑错而来的,他是把鲁迅早期的译本作为一种学术现象来探讨,他提醒说:“原文和译文之间这种出入给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6]
卜立德的《为豆腐西施翻案》属于带点“戏谑”色彩的论文,他主要是不满中国大陆学术界和语文教育界把鲁迅《故乡》中的人物豆腐西施视为反面角色,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卜立德分析了造成误读的两个原因:粗心的读者以为,既然与作者姓名有一字相同之小说叙述者“迅”不喜欢豆腐西施,那鲁迅就不喜欢她;带阶级偏见的读者认为鲁迅爱贫穷的闰土,不喜欢小市民豆腐西施。其实叙述者“迅”不是鲁迅本人,豆腐西施也不比闰土道德低下,闰土见到“迅”恭敬地叫“老爷”,而豆腐西施见了“迅”仍然称呼她的小名“迅哥儿”,还挖苦“迅”贵人健忘,可见她比闰土有勇气面对发迹后的“迅”。而且她拿东西也是当着“迅”的面拿,算不上偷。倒是闰土偷偷在灰堆里埋碗碟,败坏了“迅”对他少年时代的良好印象。卜立德认为豆腐西施接近鲁迅杂文《阿金》中的主人公,她们显得很泼,鲁迅实际上对阿金式的“泼妇”有所赞赏,肯定她们的野气和胆量。[27]
卜立德上述观点未必都能够说服别人,真正让人叹服的是,作为一名英裔学者他能够非常自如地运用汉语写出上述论文,而且还能够写得那么俏皮幽默。相比之下,许多欧美和日韩中国学家由于对汉语掌握不够娴熟,写起汉语文章总带“老外腔”。这当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由于不精通汉语,不少外国的中国汉学家读不懂、看不透鲁迅的作品,在他们的论著中就难免出现了一些误读。不过,这也是跨文化交流中必然出现的事,想完全避免也难。
2002年,卜立德用英文写作的《鲁迅正传》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28],该传记分17章叙写鲁迅自出生到死亡的生命历程,《鲁迅研究月刊》登载过黄乔生翻译的这部传记的第十章[29]。卜立德在传记的前言中交代,鉴于过往的鲁迅研究专著对鲁迅称赞的占绝对多数,他准备采取一种公正、公平的态度来写鲁迅传,应该说他基本完成了这一预设目标。这部鲁迅传除了叙述比较平稳、理论比较持平外,具体写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正如黄乔生所言,卜立德“很注重使用细节和实证材料,也很注重传主的生活环境的再现”[30],这种写法恐怕值得大陆学者借鉴,因为我们的鲁迅传记中有太多对时代风云、社会背景的“宏大叙述”,而忘记了鲁迅首先是一个有血肉的人,也是一个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人。
本时期法国的鲁迅研究显得步履维艰,原计划出版的8卷本鲁迅作品集因资金问题未能出版,这对法国鲁迅研究者来说应该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尔·露阿等“鲁迅小组”中的学者一如既往地热爱和研究着鲁迅。米歇尔·露阿给中国的刊物寄来《敬隐渔名字的来源》[31]这样的考据性文章,解释20年代最初把鲁迅的《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的敬隐渔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个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义和象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90年代中期,米歇尔·露阿为中国画家裘沙、王伟君的《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32],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画的《鲁迅之世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翻译工作,比起把汉语的鲁迅作品译成法语并不会容易,这种特殊的翻译“是两种感觉方式之间的纽带,两种文化之间思想沟通的桥梁,它是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32]。她认为裘沙、王伟君的画面常常“象闪电一般将鲁迅深刻的思想内涵揭示在我们面前”,她感谢画家辛勤的劳作使人们更容易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
法国出版的一部名为《浪漫的现代中国:1918-1949》[33]的著作,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描绘20世纪前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其中对鲁迅的创作多有阐述,值得注意。
德语世界对鲁迅的研究并不寂寞,一些热爱鲁迅的学者在默默做着研究工作,奉献了自己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瑞士学者冯铁的论文《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时间运用——以鲁迅等作家为例》[34],引用了鲁迅的小说、书信、日记的时间记录方式,对其特点进行讨论,试图探寻民国时期中国的时间记录方法及其所包含的历史意识、象征意义,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日期记录没有任何线索,时间的进行是模糊而不规则的,这实际上符合精神病人对时间的感应。
1994年在瑞士联合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鲁迅选集》,选集的主持者是德国沃尔夫冈·顾彬,他撰写了长篇后记[35],后记对他本人学习汉语,走向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之路的历程作了勾勒,对德国学者翻译鲁迅作品基本情况作了回顾和评价,对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各类作品作了细读,中间穿插了对欧美鲁迅研究成果的评价。顾彬说西方鲁迅研究经历了波折后,不少学者在1989年之后终于确定了这样的研究原则:“既反对视鲁迅为纯粹革命者的正统观点,也反对将鲁迅视作虚无主义者的反教条主义的观点”,“我们试图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种折中的理解”。[35]顾彬指出,“时代精神的批判性分析无疑是贯穿鲁迅作品始终的一条红线,而长久地坚持独立性也使作家付出了代价:寂寞、厌烦或者说是无聊的苦闷”纠缠着他;鲁迅作品“应该被看作是关于希望之可能与否以及忧郁的艺术的一种疏离的、自嘲的话语”。[35]在分析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时,顾彬深刻地指出,“离题是鲁迅散文至今未被认识的一个风格技巧:不追随某一个既定的主题,作者运笔是如此地散漫,以致于失去了他的描写对象”[35],他认为散文化的小说《社戏》就是这样作品的典型。
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语出版了《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36]一书,它的作者张钊贻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教师(他在1987年出版过英文著作《尼采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该书分五章论述问题:
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
二、奴隶价值的重估;
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
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
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该书最后的结论是:“通过融和现代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力量’,鲁迅把尼采带给中国,把中国带向世界。”[37]
90年代初以来,冷战格局的终结使西方鲁迅研究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上一时期鲁迅研究论著中时常现身的二元对立冷战思维逐步消失,仅仅把鲁迅作品当作观照中国现代社会之范文的研究理路逐渐退出学术界,从艺术本体、审美特性、文化心理等层面研究鲁迅的文本和精神结构成为基本学术趋向,尤其是对鲁迅作品作艺术本体的阐释之风气日益浓厚,这一切都表明:鲁迅越来越被当作文学家看待,表明鲁迅研究在这些国家正日益走向深化。希望90年代以来西方鲁迅研究的学术思维、观察视角、研究方法,能够为国内的鲁迅研究者提供参考和启发。
注释:
①本文把这三个区域的国家统称为西方国家。
【参考文献】
HuangWeizong.TheInescapablePredicament:TheNarratorandHisDiscoursein"TheTrueStoryofAhQ"[J].ModernChina,16,4(October1990).
YangShuhui.TheFearofMoralFailure:AnIntertextualReadingofLuHsun''''sFiction[J].TamkangReview,21,3(1991).
林毓生.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含义——兼论“国民性”问题[J].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8).
TangXiaobin.LuXun''''s"DiaryofaMadman"andaChineseModernism[J].PMLA,107,5(1992).
DavidDer-weiWang.LuXun,ShenCongwen,andDecapitation[A].InX.TangandL.Kang,eds.Politics,Ideology,andLiteraryDiscourseinModernChina:TheoreticalInterventionsandCulturalCritique[M].Durham:DukeUP,1993.
ZhangLongxi.RevolutionaryasChrist:TheUnrecognizedSaviorinLuXun''''sWorks[J].ChristianityandLiterature45:1(Autumn1995).
Yi-tsiMeiFeuerwerker.Text,Intertext,andtheRepresentationofSelfinLuXun,YuDafu,andWangMeng[A].InE.WidmerandD.Wang,eds.,FromMayFourthtoJuneFourth:FictionandFilminTwentieth-CenturyChina[M].Cambridge:HUP,1993.
BentonGregor.LuXun,LeonTrotsky,andtheChineseTrotskyists[J].EastAsianHistory7(1994).
[9]YueGang.LuXunandCannibalism[J].InTheMouththatBegs:Hunger,Cannibalism,andthePoliticsofEatinginModernChina[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9.
[10]KaldisNicholas.TheProsePoemasAestheticCognition:LuXun''''sYecao[J].JournalofModernLiteratureinChinese3,2(Jan.2000).
[11]ShihShu-mei.EvolutionismandExperimentalism:LuXunandTanJingsun[A].InShi,TheLureoftheModern:WritingModernisminSemicolonialChina,1917-1937[M].Berkeley:UCPress,2001.
[12]PaulB.Foster.TheIronicInflationofChineseNationalCharacter:LuXun''''sInternationalReputation,RomanRolland''''sCritiqueof''''TheTrueStoryofAhQ,''''andtheNobelPrize[J].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13,1(Spring2001).
[13]WangBan.IronyandSocialCriticisminLuXun''''sFiction[A].RhetoricoftheAbsurd:theGrotesqueinYuHuaandLuXun[A].InWang,NarrativePerspectiveandIronyinSelectedChineseandAmericanFiction[M].Lewiston,NY:EdwinMellen,2002.
[14]JamesReevePusey.LuXunandevolution[M].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8.
[15]MaryAnnFarguhar.Children''''sliteratureinChina:FromLuXuntoMaoZedong[M].M.E.Sharpe,Armonk,NewYork,1999.
[16]EdwardGunn.RewritingChinese:styleandinnovationintwentiethcenturyChineseprose[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1.
[17]MarstonAnderson.Thelimitsofrealisim:chinesefictionintherevolutionaryperiod[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期的中国小说[M].中译本(姜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8]LydiaH.Liu.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China,1900-1937[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M].中译本(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19]李天明.难以言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0]Davies,Gloria.TheProblematicModernityofAhQ[J].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3(1991).
[21]JonKowallis.TheLyricalLuXun:aStudyofHisClassical-StyleVerse[M].HawaiiUniversityPress,1996.
[22]JonKowallis.FestivalsforLuXun:The"LesserTradition"andNationalIdentityConstruction[J].ChinoperlPapers:ChineseOralandPerformingliterature20-22(1997-99).
[23]JonKowallis.LuXunandGogol[J].TheSovietandPost-SovietReview,27:2(2000).
[24]BonnieS.McDougall,KamLouie.TheliteratureofChinainthetwentieth-century[M].HurstandCompany,London,1997.
[25]卜立德.《呐喊》的骨干体系[J].尹慧珉译.鲁迅研究月刊,1992,(8).
[26]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J].鲁迅研究月刊,1993,(1).
[27]卜立德.为豆腐西施翻案[J].鲁迅研究月刊,2002,(5).
[28]DavidE.Pollard.TheTrueStoryofLuXun[M].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2.
[29]卜立德著,黄乔生译.转变中的鲁迅:厦门和广州[J].鲁迅研究月刊,2003,(3).
[30]卜德著,黄乔生译.转变中的鲁迅:厦门和广州“译后记”[J].鲁迅研究月刊,2003,(3).
[31]米歇尔·露阿.敬隐鱼名字的来源[J].鲁迅研究月刊,1995,(6).
[32]米歇尔·露阿.《鲁迅之世界全集》作序[J].鲁迅研究月刊,1996,(1).
[33]ZhangYinde.Leromanchinoismoderne1918-1949[M].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2.
[34]冯铁.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时间运用——以鲁迅等作家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1998,(11)(译者李良元).
[35]沃尔夫冈·顾彬著,梁展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文集〉后记[J].鲁迅研究月刊,2001,(5).
[36]Chiu-yeeCheung(ZhangZhaoyi).LuXun:theChinese"Gentle"Nietzsche[M].Frankfurt,etal.:PeterDang,2001.
[37]冯铁著,萧婉译.书评三篇·《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J].鲁迅研究月刊,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