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范文
时间:2022-05-22 08:4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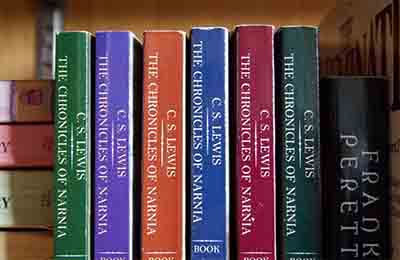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此说较为客观公允。然而,班固对屈原及《离骚》并未完全否定,实际上也有肯定甚至高度颂扬之处。《离骚序》又云:“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2]89班固肯定了《离骚》“弘博丽雅”的文辞及其在赋史上的地位,后来的辞赋作家如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莫不受其沾溉,驰骋文辞,取其英华,尊其范式,奉之为圭臬,然终不能及。班固在《离骚赞序》一文中对屈原的遭遇、《离骚》产生的背景及题旨加以详细论述,多有颂扬之词,这与《离骚序》中的有些观点差别很大。《离骚赞序》曰:《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终不觉寤,信反间之说,西朝于秦,秦人拘之,客死不还。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
班固结合《离骚》《九章》产生的社会背景,站在同情屈原遭遇的立场上,猛烈抨击楚国的黑暗政治,极力歌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作品的抒怀讽谏意义。《汉书•地理志》亦曰:“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奏记东平王苍》又曰:“昔卞和献宝,以离断趾;灵均纳忠,终于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篇,万世归善。”在其他篇章中,班固也多次对屈原及其作品予以肯定甚至赞扬,如《汉书•艺文志》曰:“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作者将《离骚》与《诗经》相提并论,高度赞扬了其强烈的讽谕劝谏功能。
与对屈原及《离骚》的评价相似,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的评价也充满了矛盾,既体现出正统儒学的传统保守观念,又表现出理解同情的态度,因此也是批评与颂扬并存。《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一方面,班固从正统儒学的思想观念出发,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没有依经立义,故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弊端。班氏的这一思想来自于扬雄论《史记》“是非颇谬于经”及其父班彪《史记论》中的观点,当然,这与班固屈服于统治者的政治压力也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司马迁突破传统儒学来评价事物,恰恰是他的进步,班固对《史记》的评价,无疑体现了正统儒学对文人至为深刻的影响。另外,由于创作《汉书》时受到上层统治者的直接干预,因此班固对封建正统思想不敢有丝毫的超越,而是极力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并以其是非为是非,将文学创作完全纳入政教轨道之中。另一方面,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又有所肯定。他承认司马迁是“良史之材”,肯定《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的叙事及语言特点。尤为重要的是,班固还进一步指出《史记》具有“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特点。他认可司马迁的实事求是、秉笔直录、爱憎分明、褒善贬恶的创作原则的同时,其实从侧面也展示出自己撰史的标准。班固以《小雅•巷伯》比附《史记》,对司马迁“既陷极刑”“发愤著书”的经历表现出理解、肯定及同情的态度。然而,班固认为,司马迁虽“博物洽闻”,却不能“以知自全”,故又从正统儒学的角度指责司马迁不能明哲保身。
关于辞赋的批评
班固为东汉著名辞赋家,他不仅撰写了一些辞赋,而且发表了诸多颇有价值的赋论。由于受儒家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班固的赋论往往从维护、巩固封建统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角度出发,而且掺杂有谶纬迷信的成分,因此表现出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当然,班固对汉赋的源流演进、艺术特点、功用、对具体赋家的分析评价、对赋体的分类等,也体现出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两都赋序》云: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总体看来,该序对汉赋作出了较高的评价。班固称赋为“古诗之流”“雅颂之亚”,这更多地是从赋的讽谕意义着眼而论的,也就是说,赋具有同《诗经》一样的讽谏功能。班固认为,汉赋能够为汉帝国“润色鸿业”,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谕”,又可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就把刺过与颂美结合起来,真正贯彻了儒家文艺观的美刺主张。过于强调辞赋为统治者润色鸿业的颂美作用,势必会把歌功颂德当成辞赋的一种社会功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班固把汉赋看作大汉文章的正宗,并进一步指出统治者的爱好与提倡对辞赋走向繁荣的促进作用。上有所好,下必追趋,文人“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自武帝至成帝,“言语侍从之臣”大量涌现,形成了汉赋的作家群。这一时期,奏御之赋达一千余篇,创作盛极一时。此序也体现出班固的谶纬迷信思想,为迎合东汉帝王的好尚,班氏称“众庶悦豫,福应尤盛”,此“福应”即指祥瑞之事,亦即序中所述“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举凡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或统治阶级有意做出的与祥瑞有关的事情,都标志着王朝有福应和瑞兆。班固在序中所言福应,实属为东汉王朝歌功颂德之语。在对具体赋家司马相如的分析评价中,班固似乎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有时批评否定,有时却又肯定颂扬。《汉书•艺文志》曰:“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
《汉书•叙传》也称司马相如“文艳用寡”“寓言淫丽”。班固认为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过于讲究华丽辞采而缺乏《诗经》的讽谕之义,因此应该予以批判,显然这是从儒家的政教功利文艺观出发而论的。然而,班固在很多情况下对司马相如等人又加以肯定甚至颂扬,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直接引用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语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的讽谏功能,并对扬雄的观点加以批判:“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一方面,班固认为司马相如赋中有“虚辞滥说”,其实是不太认可赋中的虚构夸张手法,另一方面,又从批判扬雄的观点出发,肯定了司马相如赋的讽谏意义。这种自相矛盾的评价也体现在《汉书•叙传》中,如上所述,班固指责司马相如赋“文艳用寡”,而又提出“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的观点,可见存在着矛盾。“托风终始”即说相如赋具有讽谕劝谏的社会作用,“多识博物,有可观采”又指出相如赋具有认识事物的作用,而“蔚为辞宗,赋颂之首”则给予其极高的地位。关于辞赋的分类,班固《汉书•艺文志》继承了刘歆《七略》中的观点,将辞赋分为四类:第一类首列屈原赋,下有唐勒、宋玉、赵幽王、严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20家赋,共361篇;第二类首列陆贾赋,下有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萧望之、扬雄等21家赋,共274篇;第三类首列孙卿赋,下有秦时杂赋、李思、刘越、长沙王群臣、李忠、贾充、张仁等25家赋,共136篇;第四类首列《客主赋》,下有《杂行出及颂德赋》《杂四夷及兵赋》等12家,共233篇。班固对辞赋如此分类,却未提及分类依据,故后世学者多有猜疑。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曰:“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章氏治学,特重区分流别,然亦未能指出屈原、陆贾、荀卿三家赋的区分标准。其《校雠通义》卷三亦曰:“《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每略各有总叙。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抑流传之脱简邪?”据章氏之言推测,《诗赋略》如有叙论,其中或许应该包含分类依据。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则说:“《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曰屈原赋,二曰陆贾赋,三曰孙卿赋,四曰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七略》相如赋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
此说指出,扬雄赋与司马相如赋有直接的继承关系,班固既列司马相如赋于屈原赋下,则不当列扬雄赋于陆贾赋下。这一观点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班固为何如此归类却未予以探讨。刘师培则试图对班固关于辞赋的分类依据加以说明,其《论文杂记》说:“自吾观之,客主赋以下十二家,皆汉代之总集类也;(此为总集之始。)余则皆为分集。而分集之赋,复分三类:有写怀之赋(即所谓言深思远,以达一己之中情者也),有骋辞之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有阐理之赋(即所谓分析事物,以形容其精微者也),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刘氏提出写怀、骋辞、阐理可能是班固区分辞赋的依据,这完全符合汉代赋体文学的实际情况,但对于各类所属的赋家是否都具有相应的创作特点,却没有进一步探讨。据实而言,上述依据与其所属的赋家风格并不完全吻合,这是因为汉代赋家的创作题材极为广泛,风格亦灵活多样。综上可知,班固并非单纯以赋作题材、风格作为分类的标准。
对诗歌、小说批评理论的阐发
班固对诗歌的产生、性质及功用的论述,基本继承了儒家文艺的传统观点,又结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予以一定程度的发挥。《汉书•艺文志》云:“《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礼乐志》又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这些论述基本沿袭了《礼记•乐记》及《诗大序》中的观点。诗人主观情志受到客观外物(包括社会现实)的刺激而有所感应,故而形于诗歌,从而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诗言志”一说本源于《尚书•尧典》,明确指出诗歌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关于诗歌的社会作用,班固承认诗歌可以反映社会风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统治者可以据此了解民风民情民声,以便及时自省与调整,从而进一步巩固统治,而下层民众也可以据此抒发真实情性。一旦王道衰落,朝政不兴,民众必定有所指斥,故《汉书•礼乐志》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
由此可见,诗歌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心志之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作用在汉乐府民歌中体现得也很突出。《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班固指出汉乐府民歌都是有为而发,是人们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种哀乐之情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更是直接明确地体现出诗歌与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班固在《汉书》中还曾论及各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等对诗歌风格的重要影响。《汉书•地理志》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特定的地理环境及生活条件促成了特定的社会风气,这种特定的社会风气必然影响到诗歌的风格。秦国地处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杂居,战事异常频繁,《诗经•秦风》中多有秦地人尚武精神的表现并非偶然现象。至于《诗经•豳风》,班固则强调其人以农为本的民族传统。《汉书•地理志》又曰:“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诗经》《史记》所载,周民族的先祖后稷、公刘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以农立国,逐渐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民族传统。《诗经•豳风•七月》形象地描绘了周部族农民全年辛勤劳动的场景,可以说是豳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再现。又如《汉书•地理志》论“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云:“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內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鄁,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临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庸、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汉书•地理志》论《诗经•唐风》则曰:“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梦帝谓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之参。’及生,名之曰虞。至成王灭唐,而封叔虞。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又论《诗经•郑风》云:“郑国,今河南之新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诗经•郑风》《卫风》中的爱情诗数量颇多,亦当与其地的民风民俗、生活习性不无关系。诸如此类的论述在《汉书•地理志》中还有一些,虽不能说全部正确,但也无疑反映出班固一定的识见。除诗、赋二体外,班固还论述过“小说”一体。《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班固指出,小说属于稗官野史,本源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故与圣贤经传著作等“大道”迥然不同。班氏还认为,先秦诸子十家,可观者九家,可见有意把小说排除在外,这反映了儒家正统文人对小说的歧视。然而,西汉小说创作的发展现状又使得班固对其有所肯定。小说既出于民间,自然可以反映民意,对于上层统治者维护巩固统治、下层民众抒发心志都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样一来,班固又提出小说如同“刍荛狂夫之议”,有其“一言可采”之处,故“必有可观者焉”。尽管这种肯定仍然是援引孔子的话来间接表达出的,但不可否认它所体现出的班固对小说这种文体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作者:刘涛单位: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 上一篇:文学批评类型的转换范文
- 下一篇:文学批评的多元化状态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