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节点的确立范文
时间:2022-10-22 09:16: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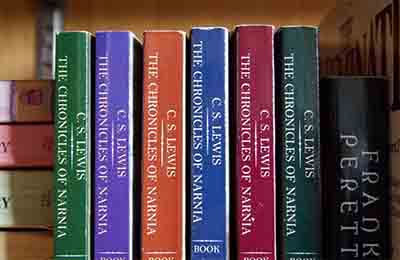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江海学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文学史是文学演化过程的历史记载。作为历史的记载,它需要对历史过程有连贯性的把握,即前面某一时代的状况影响了后来的历史阶段,后来历史阶段的新变革在此前某一时代已经孕育了胚芽。此外,文学史作为历史述录的一个方面,它还需把握历史的跃升,后来时代较之于此前有了一些新质的嵌入,才达成了历史的转折、转型。而且由于这种转型不只是公元纪年数字上的增加,才真正构成了历史的演进。在不同的学科、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历史,不难发现众多不同性质的重要节点。由是观之,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范畴,它自身也有一些重要节点。而这些节点所具有的性质、发挥的作用、如何定位等等,成了我们需要考察的问题。本文不作全面探讨,主要从如何确定文学史的节点来进行论析。
一、时间尺度:分期作为节点
作为从历时角度研究文学的学科,文学史中的时间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既要把相关的文学纳入时间框架,还要尝试通过对时间过程的分期来体现对史实的述录。譬如,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在教科书体系中一般被定为1919年“”。这样一个时间分期,可以比较方便地解说中国现代文学所表达的启蒙主义意识,能够把20世纪20年代以后各种如火如荼的文学运动纳入到新思潮的框架,而这些新思潮与“”的思想诉求密不可分,因此这种分期被沿用多年。以往文学史多根据朝代更迭分期,如唐代文学、宋代文学等等,如果仍以另外一个节点步入当代文学,则又是回到了“改朝换代”作为分期的依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就可以另外一些标志作为参考。例如辛亥革命是一个选项,它推翻了满清,直接就是文学的方便分期,由此来看,就应该把1911年或次年的1912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年份。此外,胡适、陈独秀在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上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相关文学观念有所表述,起到了现代文学的“催产婆”的作用,未尝不可把1915年作为时间起点。再往前溯,1905年清朝废除实行了千余年、对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举制,这也影响到文学,何尝不能把这作为新文学的起点?如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缘起,需要结合中国历史状况思考,而这种状况显然和中西文明冲突有关,那么这个时间点就贯穿了整个19世纪。而在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看来,文学启蒙和变革的思想其实早在清末就已经出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①。因此,晚清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时间起点。文学史的时间分期节点是最为直观的存在,实际上人们把握时间就是以一些分期作为节点的。譬如某月某日某时,时间的刻度既是作为事件的标记,也是事件内涵的背景,某一时间作为节庆时刻,节庆的欢庆场面与当时发生的具体事情无关,只是因为它处于这个事先已经规定为节庆的时间,就应该有欢庆气氛。假如有人遭遇与节庆气氛不融洽的事情,只能暂时撇开,节后再来理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的节点自身就可以体现意义。
当然,时间标记作为历史的记录坐标,还有具体的文化层面的价值。譬如1784年英国蒸汽机工程项目,在瓦特等科学家看来,蒸汽机车带来的机械动力,数倍于之前的人力和畜力,意味着强大的力量。事实证明,正是依靠蒸汽机车的动力系统,英国建立起了强大的海上武装。同时,由于蒸汽机车的发明和使用,原先一些可能只是平民的人,被擢升到了国家权力体系中,组成了一个新的阶层———资本家,他们的出现使得旧有的贵族统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蒸汽机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发明,就可以作为历史考察中的节点,把此前和此后的历史阶段分别看待。其实,历史节点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是有构设的,只是不一定自觉。譬如在家喻户晓的武松打虎故事中,武松和老虎两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武松打死老虎成了英雄传奇。而今天老虎在世界各国都是一级保护动物,法律条款规定要尽量地保护老虎,回头再看武松和老虎之间你死我活的场面,故事将被当做一个悲剧,因为其中任何一方的死亡都令人悲伤。虽然该故事如今仍然作为一个英雄传说继续流传,但具体的对于真实生活中的老虎则必须采取另外的视点,并不直接与武松所打的老虎对接。在文学史上,时间节点会以不同的面貌呈现。有时一位杰出的作家就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有时一部作品或一种风格的作品成为时代标志,有时一种文学思潮或文学社团的出现,能把文学的变革推到醒目位置,变成文学史的节点,更多时候则是依托于一般的时代分期,如我们常说的盛唐诗歌、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等,某个时代的文学就鲜明地体现了所在时代的特色。
文学史的时间节点除了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意义,它也可以超出文学史的范围,进入到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层面。如近代是社会和文化都有着重大转型的时期,这种转型也体现在文学及文学研究领域。朱光潜先生曾经把文艺典型作为文学研究和美学中最基本的关键词来把握,而该词的涵义并非与历史一脉相承,他说:“总的说来,18世纪以前西方学者都把典型的重点摆在普遍性(一般)上面,18世纪以后则典型的重点逐渐移到个性特征(特殊)上面。所以18世纪以前,‘典型’几乎与‘普遍性’成为同义词,在18世纪以后,‘典型’几乎与‘特征’成为同义词。”②应该说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在18世纪以前注重的是共性一面,此后则是注重个性一面。这种差异在面对古典文学作品时,主要体现为所强调的内容差异,如同样都认为荷马史诗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古代的批评主要凸显那些典型的普遍性意义,而现代的批评则侧重分析典型的个性表现。因此,把18世纪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来理解文学典型观念的变化,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不过,所谓节点并非那个时间点自身就具有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相应的思想框架才把某一时间点作为节点来看待的,不同的着眼点会看到不同的时间节点。譬如在美国学者奥康纳看来:“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19世纪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③在他的表述中,18世纪被划到了古代传统的阶段,19世纪才具有了开启新时代的意义,并且自此之后历史演化有了一种加速度的变化节律。既然文学史涉及分期,长达数千年的民族文学史就需要通过分期来把握各时间段的主要问题。而围绕一些作家、流派的几十年的文学史发生过程,也往往需要厘清时段,梳理出发展脉络。
其实就研究对象自身的情形来说,当时的状况也许是此前此后人们并不一定能感受到决定性的变化,而后来的研究者通过对文学演变走势的分析,从中看到某种在当时也许并不被人认为重要,而在研究者看来则是具有决定性作用、影响到了整体演变趋势的因素。正如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所说:“中唐时,一种相对新颖的创作观念凸显出来,勾连了自然与技巧两方面。诗的一联或一行渐渐被看作是某种意外的收获,它们先是被‘得’到,而后通过深思熟虑的技巧嵌入诗中。这一新的流行观念对于理解诗人经验和创作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意义。”④宇文所安所提及的“得”,并不是指简单的心有所得,而是呕心沥血思考之后产生的灵感,在此方面他所说的“中唐”时期贾岛的事例就特别典型。贾岛曾经写有《送无可上人》一诗,全诗为: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按照律诗格式的规定,全诗八句,其中间四句要构成两副对联,作者贾岛特别看重第二副对联,即全诗的第五、六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贾岛在该诗旁附一首《题诗后》的短诗作注,其中两句为“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对上述第五、六句的自评。这“二句三年得”中的“得”,才是中唐时期所强调的“心有所得”嵌入诗中的恰切意思。再进一步看,强调心得然后要求通过一定的技巧加以展示,就是中国诗歌中的“炼字”,这种写诗的方式确实是唐代以后才盛行起来,并且成为写诗的必修课。那么宇文所安所划定的“中唐”这个具体的日期就可作为时间节点,但其实这个节点是可以商榷的,并不只是唐代才有了炼字,在南朝时,谢灵运作《登池上楼》诗云:“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其中春草是“生”而不是“长”,其实“长”是一个更容易让人想到的词汇,但不采用“长”而用相对冷僻的“生”,也表达出了“长”的含义,同时可以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生”还可以有生气勃勃等附加的意思,可以说在该诗中就隐隐可见炼字的痕迹。因此,真实的文学世界中,由早先强调“诗言志”、“诗缘情”那种有感而发,是把诗所表达的内容作为最核心的东西,转换为有所“得”,即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所指,而是如何通向所指,把日常表达转化为具有诗意的表达、有意境的表达,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但是,我们也要理解历史的进程需要有一些时间节点来加以把握,否则我们的思维无法注意到缓慢过程中的渐次变化。如果要寻觅一个时间作为转换的节点的话,则中唐时期可能就是合适的选择。正所谓理论和现实之间有距离,但用理论来阐明现实总是学科研究的通常归宿。
二、文学标杆:经典作为节点
文学史可以是以往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流水账的形式来展现,一些所谓注重史实材料的文学史具有一些此类的倾向,但即使是流水账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包罗所有的文学史实,譬如一个朝代可能存留下来了若干首诗作,它们可以被作为档案材料加以保存,可是不能都在文学史著述层面加以论述。这种“不能”既有“不必要”的意思,因为其中的大多数诗作了无创意,显得雷同平庸,对其具体评述没有多少价值还冲淡了整个研究的主题和亮点;也有“不可能”的意思,因为如此多的诗作,仅其作者姓名和诗名的篇幅就不是一般的研究著作可以容纳的。因此,文学史的研究和著述需要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加以选择性的关注。要选择就涉及选择的标准。各家各派的文学思想各不相同,因此标准也不可能统一。大体来看,有两种类型的文学可能成为文学史关注的对象。第一种是可以作为文学中的事件性质的类型,它不一定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也不一定具有征服读者的效果,但是它的出现成为了文学变革的风向标。譬如“初唐四杰”的多数作品和盛唐时期的诗作之光焰四射相比,只能算是晨光熹微,甚至与此前的六朝诗作相比,也并不能说就有更大成就,至少在影响力方面有所欠缺。
但是,盛唐以后诗作的荣耀必须要有一种历史的演进轨迹才能得以正名,那么“初唐四杰”就成了当然的不二之选。同样道理,现代文学史中胡适的《尝试集》也有相似的情形,它的出版代表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诞生,可是新生的往往也就是稚气未脱,并不出色,所以连胡适自己也说《尝试集》中除了一两首还差强人意之外,其余的都是不成熟的作品。但《尝试集》已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个中缘由不在于它是否优秀,而是它作为开拓者,开启了后来的诗歌创作路径。第二种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即文学史的优秀作品入选文学史的讲述范围,其中顶端的杰作是经典作品,那就不仅是自身的优异令人叹服,而且还作为引领文学潮流的标杆,标志文学总体水平的参照坐标。这种对于优秀作品和其中顶端作品的膜拜,既是一种对于权威的认同,同时更是一种建立文学秩序的方法。对于文学作品已经有了很多色彩斑斓的表达,而且新的表达层出不穷,如果仅就其中的不同来做出认知,那么文学的研究就如同面对变幻莫测的万花筒世界,难以找到其中主导的、标志性的、规律性的东西,而文学研究的迷惘也会使一般的文学阅读缺乏引导性的意见作支撑,文学创作方面也就没有创作之外的意见反馈出来,整个文学活动就缺乏意见的交流模式,很大程度上只算是创作者单独的表达,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成为了自言自语,而这样的局面对于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都是极其不利的。同时在研究领域上的缺失,也就使得人们在审视世界和自身时,缺少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对经典性作品的认定,以及把经典作品作为文学史中的标志性作品加以重点研讨,其实不仅是对该经典作品的深入思考,更是一种把五光十色的文学系列整合起来的努力,相当于确立文学坐标系统中的原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学经典的确立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因此,当文学史提出某些作品作为经典的时候,可能与当初该作品面世的时候被人们所认同的情况已有不同。文学史上极为著名的事例是陶渊明的文学地位问题。在他所生活的晋代,陶渊明都没有得到很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仅把陶渊明列为“中品”,在当时这种安置并没有被认为不妥。可是唐宋之后,随着平淡精炼的诗歌美学追求日益突显,陶渊明逐渐被擢升到了经典级别的诗人的位置。文学史要采取经典化的方式来叙述过往的文学,那么经典作为价值评判的结果,就必须要有撰史者的立场的嵌入。因此,所谓文学史的客观性作为一个原则不能不加以强调,否则就不能被纳入学界公认的文学史基本框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又确实不是都能够做到,并且对于这种背离也基本上可以得到学界的部分默许。对其把握的尺度大体上是事实层面的讲述必须坚持客观性,而在评价层面则不必固守当时条件下人们的认知状况和审美取向。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内在矛盾的秉持,和人文研究领域的基本状况有关。丹尼尔•贝尔认为,人文领域并不是研究者站在一个完全中立的立场不动声色地来描述相关现象,他往往还有一种想要干预所发生的事件的冲动,这一内心的秉持就使得人文研究领域在最初的选取事实加以表述的时候就有了一些主观态度,因此在人文研究著述中,“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历史是事件的变迁,而社会是许多不同关系织成的网,这些关系是不能只靠观察来认识的”⑤。文学史作为人文研究的一个方面,它需要重现过去时代文学的实际状貌,同时更需要把握今天来如何面对过去时代、人们如何来表达情志、如何营造审美氛围的问题,因此,在客观事实的方面尽量尊重事实本身之外,也要站在今天立场来对过去做重新定位,这是无可指责的。克罗齐曾经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体上也是这个意思。
三、文化转型:文体与文类作为节点
文学之为文学,不是因为它具有某种基本性质,有之就使得它成为文学,无之则不是文学。文学最确定的存在对象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被文学地看待才是它成为文学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学除了作为人所制作出的产物,它还是人所认定才具有的资格。有些作品本来自有专门用途,而文学则是“无用”的,即柏拉图所说的没有专门用途的。譬如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庄子和孟子的散文,以及作为史书的《史记》、《左传》、《国语》等,按理不在文学的范围内,可是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它们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堪称文学中的经典。历史著述基于事实的记载,而文学则鼓励想象和虚构,本来两者之间有较大差异,但是这些史著文笔很好,而且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史著的叙事充当了本应由叙事文学来达成的目的,再则史著中有“春秋笔法”,言在此而隐意于彼,它和文学中的表达高度相通。这些作品作为文学的理由是充分的,可是它们并非纯粹性质的文学毕竟也是事实。到了近现代,那些写得很好的著述还是可能被看成文学,曾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专业领域内是历史学家,可是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理由也是从语言表达的艺术性来看的。但是当今的文学观念有了分层次的思路,往往更倾向于康德的没有目的性实用性的层次来理解纯文学,而另外一种和政治、社会等联系紧密的也是文学,但就不算纯文学。作者必然生活在具体的时间空间中,完全符合标准的纯文学可能并不存在,但是在理论上可以假设它的存在,就可以把具体的作品与这种纯文学之间的差距作为一个考察的方面。在此角度看来,以前的史著可以是文学,并且可能因其文笔的优美以及思想上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被树立为文学中的典范,而在今天一般并不是这样来认知,史著是以材料的可靠性和见识的深邃作为评价其价值的指标,文学则允许虚构,甚至允许作者的见识并不一定是真知灼见,只要他的作品可以给人语言的享受和心灵的抚慰。在文学沿革的轨迹中,文学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字表达、思想诉求、美学追求、写作出来之后已经定型但是不同时代对该作品完全不同的领会,等等。实际上人文领域中的一些问题,人们从一个角度看到的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的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而这种不同都具有合理性。譬如奥威尔(G.Orwell)和赫胥黎(A.Huxley)两人都对于现代性影响下的文化问题表达过一种担忧:“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⑥一般说来,奥威尔具有一股现代派诗人的思想特质,而赫胥黎更像是一个后现代的思想家。把这样一些差异性的认识并置起来的时候,似乎它们水火不容,可是当时提出各自观点的时候,它们都有其合理性。当文学在整个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变化的时候,不同研究者可以从不同方面或角度看到各不相同的东西,并且可以分别从文学自身或者从社会角度来分析引起变革的原因。
如果要比较客观,在可以重复、可以相对量化的层次上来考察文学的变革,应该是把文体作为焦点,因为文体是形式化的可以指认的客体,同时文体又是形式化了的内容,在文体的形式下面包含了内容上的相关要求,譬如格律诗要求的声律、句式等,是一整套的美学规范的具体化。当年巴赫金指出长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叙事史诗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史诗和长篇小说虽然都是叙事,并且史诗对于欧洲近代小说的影响是肯定的,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史诗具有献祭的神圣性,也具有历史叙述的庄严感,而近代的小说则走向了接近日常生活的叙事,长篇小说中的人事物可以没有神圣性,获得了普通读者的亲近感。如巴赫金所说,在小说中,“史诗中的那种间距被打破了,世界和人获得了戏谑化和亲昵化,艺术描写的对象降低到现代生活的未完成的日常现实”⑦。同样作为叙事的文体,其中的差异不是叙事而是如何叙事,不是叙述什么而是怎样叙述。小说中会有人物语言的描写,人物语言要求个性化,即不同人物的讲话要合乎该人物的身份、性格,你要安排李逵文绉绉地引经据典说出道理深刻的话,或者安排吴用火急火燎地跳出来大声嘶喊,都显得不合理。既然小说中人各有其口,就形成了小说叙述中的众声喧哗的情形,它可能不适合祭祀性质的文学所要的众口一词的需求。在这里,不是看作者要表达什么,而是文体自身有其规定性,它在要求作品如何来进行讲述。历史上的文化转型影响到文学领域的时候,往往是通过文学的类型变化来达成效果。如果说古希腊时期的文学以史诗和悲剧作为代表,那么中世纪则以颂诗作为核心;如果说新古典主义运动的文学注重戏剧,那么作为其反拨的浪漫主义则关注诗歌和小说;如果说现代派文学旗帜鲜明地反抗传统,在诗歌小说戏剧中进行全方位的出击,那么后现代派则把反抗的神圣意味消解了,标举反抗或者倡导皈依都没有意义,后现代派也并不作全方位展示,很大程度上有些刻意绕开普遍关注的文学领域,而在影视剧本、广告词、歌词等一些相对冷僻的方面下足工夫。对这样一些文学类型加以考察,最直接的作用是有助于更好地领会作品内涵,而在更大的视野范围看,通过文类可以看到时代变迁的文学体现。文类兼含了形式化和内涵体现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文学史把握文学变迁问题的基本节点。
四、范式转换:体制作为节点
在文学史研究中,比较容易注意到作家作品,所以,文学经典、文体或文类是相对容易看到的问题,而还有表面并不引人注目实际上对于文学却又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东西,其中,就涉及文学的体制问题。关于文学体制的内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这里则是从管理学角度来说的,体制是通过权限布局来设立组织机构,权限之间具有相关性。对于文学来说,如果只有一位作者,正如鲁宾逊在孤岛上一人生存,所谓创作就是自言自语,谈不上什么体制;但假如在他有了一个陪伴者“星期五”之后,他来讲述一个故事,则就可能牵涉到了文学体制问题。譬如他讲述《圣经》中的《创世纪》,则可能和来自土著部落的星期五自幼听过的传说不一样,那么鲁宾逊就要求不是在已有不同的关于创世传说中增加一个副本,而是要用《圣经》中的讲述来取代过去的部落传说。鲁宾逊会强调《圣经》表述的权威性。这样就体现了文学体制的作用。可以说,人作为社会性的主体,人所创造的文学也具有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就涉及体制因素。假如结合文学体制来看文学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的阶段性变化。如早期文学史以口头文学作为主流,缺乏文学经典的引导,同时文学批评处于自发状态,整个文学氛围相对自由,没有多少监管的外力干预。在书面文学兴起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话,那么书面文学就可以通过文字记载达成超越作者创作的时空限制,可以由对在场的人的讲述推广为对所有人的讲述,可以把当下的瞬间、即逝的讲述演化为可以传之后世的“文章千古事”。
在书面文学这样一个“化蛹成蝶”的跃进条件下,对于文学话语的监管也就顺势出现,它可以是采取相对软性的方式,譬如对合乎社会文化秩序的,授予文学奖项,纳入政府的给养体制;也可以采取硬性的措施,如有些朝代的文字狱。在这些大的文学管理情境下,还可以有若干细节角度的差异性的举措。如设立采诗官到民间搜集诗歌,表面上这是一种文化行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要把体制外的民间话语进行招安,把搜集得来的诗歌筛选过滤,那些对既有秩序持敌意的内容会被屏蔽,再推出的则已经是有益于维护既有秩序的内容。民间文学很多是口头创作,口口相授,口耳相传,在最初的生成语境并没有相应的监管措施,而在书面文学产生之后,各国各民族都有程度不同的对文学的要求,它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道德意义上的或者简单的统治当局的政治倾向意义上的等等。工业革命以来,批量化生产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与此相应,建立了一套生产制度。如同在一般的生产领域,投资者投入的动机和预期收益相关,因此在文学的出版发行这一环节,也就有了相应的规范措施,譬如版权制度,它在保护创作者权益的同时,也是对投资者的强力保护。在美国独立之初,文化方面并未从英国的影响中完全摆脱,文学领域也是如此。由于没有语言的隔阂,英国的文学作品无需翻译就可以面向美国读者,加上文化上英国的历史影响力巨大,所以英国文学在美国颇受青睐。美国未与英国签署版权法的国际公约,英国作家的创作可以不经翻译直接在美国传播,并且出版商可以不付给作家稿酬,也就是说在法律上为盗版开了绿灯。这一情形给美国作家带来了很大压力。它迫使“美国作家把注意力转向杂志,尤其是转向最适宜于杂志的文学体裁:中短篇小说”⑧。在19世纪,欧洲各国小说作家一般是要以长篇小说作为代表性的作品,可是美国因为盗版的问题,本土作家难以依靠文学获得足够生存的报酬,所以短篇小说尤其是报刊连载形式的小说风行。我们现在可以阅读到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等长篇小说,都是先通过报纸连载取得成功之后才结集出版。所以在当时美国的文学环境下,缺乏培育长篇小说的制度性的土壤。我们再看马克•吐温的长篇作品,可以发现不断出现一些悬念和小高潮的情形,这都是因为报纸连载需要不断刺激读者的阅读欲望,而长篇小说需要考虑的鸿篇巨制的结构方面的经营则相对孱弱。
这种文学出版发行的体制原因,不仅实时地影响了美国的创作,而且还结构性地影响了对文学史上既有作品的看待和理解。罗贝尔•埃斯卡尔皮曾以《格列佛游记》和《鲁宾逊漂流记》来说明文学理解上的历史变迁。这两部堪称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的作品,其最初的预设读者不是儿童,斯威夫特通过大人国小人国等想象性质的描写来展现他对国家政治的思考,对当时的英国议会有强烈批评;笛福写出的鲁宾逊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他呈现的意义不仅是荒岛求生,而且是把现代文明传播到了文化上的蛮荒之地,作为开拓者的鲁宾逊是一个英雄。⑨且不说马克思《资本论》对鲁宾逊形象的批判,至少从儿童文学角度,鲁宾逊不是作为殖民者来受到儿童们的追捧,而是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的政治的奇遇记的主人公来看的。文学出版商有自己的经营目标,他不是追寻文学价值,更不是追寻作者意图,而是获取最大的利润,那么吸引读者才是他们所关注的,尽管可能这种关注和文学本来面貌已经分离了。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是在不同的体制下运作的。虽然作者个人一支笔一页纸就可以写作,但是写作的相关条件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读者和批评家并不是看着作者写作,写与读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作者写作是通过出版发行的渠道得以进行,那么这样一个渠道就有一些出于政治、经济、文学自身等的相关要求发挥作用。也许今天的电脑网络的写作发表可以体现出一些作者的自由,可是任何写作物的发表都会瞬间淹没在网络文字的大海之中,需要文学体制下的运作人员加以打捞之后才能得到普遍的瞩目。总之,文学从其物理角度看,是作者运笔所创作的;而从社会角度看,更属于相关的文学体制所酝酿的。不同体制会有不同的文学,既然文学体制可以成为影响文学理解的重要因素,那么文学体制变迁就有理由作为文学史中的节点。
五、研究文学史节点的意义
文学史的分期并不是简单地把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切分为较短的时段,以便通过聚焦方式来更清楚地认知文学的历史,文学史分期实际上也是一种学科的建构,通过不同的分期,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观。弗拉森有一个观点被美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所引用,他说的是:“我使用‘建构性的’这个形容词来表明我的观点,即科学活动是建构,而不是发现:是建构符合现象的模型,而不是发现不可观察物的真理。”⑩科学的认知行为是要求具有客观性、可检验性等特性的,科学活动的最典型代表是物理学,从早期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到爱因斯坦的通过所谓思想实验来提出的理论,都是在现代科学的观察、检验的框架中运行的。爱因斯坦也就因此提出,科学研究并不只是一种客观观察就可以得出见解的行为,而是要预设一种思想路径,在路径下才有观察的思路,才会得到有价值的观察结果。这样来理解文学史,它作为一个文学的时间历程,文学史中有些东西需要加以特别关注,有些东西则可以简单实录,还有一些则随其沉浮,如果被人遗忘也无须惋惜。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下,找出一些节点则可以把需要强化的方面凸显出来;在突出了的内容上,通过节点也就把它的价值、意义、影响力等也彰显出来了。
文学史可以有若干不同的分期方式,不同分期依据的不同节点还体现出不同的文学史观念和思维。海登•怀特曾经就人文学科中的历史性问题指出其中的矛盾之处,“历史研究的每一种方法都预设某种模式来解释它的研究客体,其简单的原因是,既然历史包括‘过去’发生的一切,它就需要某种可比的第三者,以此区分什么是‘历史的’,什么不是‘历史的’,此外还区分在这个‘过去’的范围里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相对无意义的”瑏瑡。怀特这段话指出了历史学并不是对于既有事实的实录,或者说即使有人认为自己就是实录,那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些内容进入历史视野而非另外一些,假如进入是一种有意的筛选,就不能符合所谓实录的本意,假如说不是有意筛选而是见什么就都记录下来了,那么见其所见本身也不是完全自然的,因为人们经常会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所见如何是和所见之前的注意力聚焦关联,它就是一种无意识的筛选。真正需要说明的不是在于是否有主观有意的筛选或者思考问题的立场,而是需要对于这些主观因素的设定理由作出说明。对于文学史,它的分期,它的历史节点等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把握,这些把握都不是天经地义,不是说就一定得这样来看待文学史,反之就会迷途。那么并不能够代表真理的这些做法为何可以采用,而且关于分期的时间划分等还可能有学者之间的学术探讨及论争呢?是不是随便采取不同分期,只要史料具有真实性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文学史的分期之类的主观行为,毕竟包含一些客观性的历史事实的依据,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这些分期的角度可以彰显不同的需要强调的东西,有些类似于几何证明中的辅助线的划定,那些辅助线并不是几何图形自身具有,而是要建构几何图形各个线条联系才假想的,当几何证明完成之后辅助线就完成了使命,分期其实也有相近的效果。文学史通过分期突出某些时间节点,而节点上就把需要澄清的问题作有力铺垫。由此,文学史讲述文学的历史进程,其中历史的演进所体现的意义等则在事件进程的叙述中得以体现。
作者:张荣翼 吴群涛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 上一篇:《乐论》中的艺术哲学思想范文
- 下一篇:事业单位档案管理信息化探讨范文
精品推荐
- 1文学与文化论文
- 2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 3文学专业论文
- 4文学价值论文
- 5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 6文学作品分析论文
- 7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利与弊
- 8文学作品论文
- 9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 10文学写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