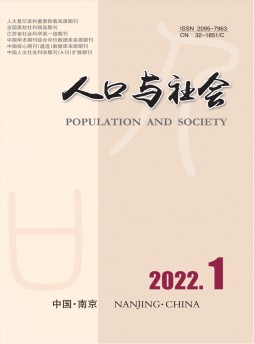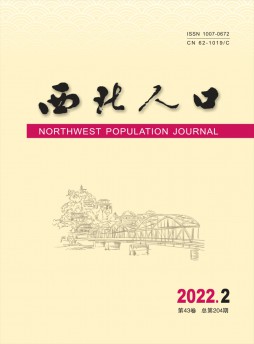人口流动生态环境范文

近几个世纪,我国一些地区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特殊形态的人口过剩。在人地紧张的压力下,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自发性人口流迁运动,以稀释其日显拥挤的人口能量。不同区域的人口消化和在对外来人口吸纳过程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确定某一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解析其人口流动的特点,进而探讨移民的经济活动与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本文主要以清代浙西山区的外区域人口流入为讨论内容,并兼及浙西山区本地的原有人口状况,探究外来移民在本地的经济活动及对该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浙西山区人口流动状况分析
据方志记载,清代浙西山区接纳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乾隆、嘉庆年间和清末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其移民活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前期移民以江、闽及本省温、处流民为主,多在山地搭棚为居,志书中称之为“棚民”或“蓬民”,如湖州长兴县,“有福建、江西棚民携妻子挟资本陆续而至,与乡民租荒山,垦艺白苎”(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严州府建德县,亦曾招“江闽无业闲民开山种麻”;而寿昌县也因为招徕了江闽流民前来垦荒,本地才有了麻、靛两种物产(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杭州府之于潜县则接纳了安庆移民,嘉庆年间有这样的记载:“邑中山多于田,民间藉以取息者,山居其半。近年人图小利,将山租安庆人种作苞芦,谓之棚民。”(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另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记载,“嘉庆初年,忽有民自他方来,云愿垦荒赁种,询所自,皆曰温州”,“山地价值不多,棚民多温处流入”。此类外来人口多向荒山野地、森林深处索取土地,开垦农田,属疆域开发型的移民。后期移民则以两湖、河南等外省民为多,在一些府县甚至超过当地土著,这类移民在志书常称之为“客户”或“客民”。《长兴志拾遗》卷下《风俗》载:“客民垦荒,豫楚最多,温台次之,农忙作散工者夏来冬去又数千人。”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亦有类似记载:“自兵燹后,本乡人少田亩荒芜,宁绍温台及两湖江北之民云集。”这些客民大多属战乱恢复型移民。
任何地区的人口问题都不是孤立的,浙西山区既然有外来人口的吸纳,就必然关联到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出。探究其人换,首要关注的是人口流出的原因,这是一个“源”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越来越多,而集中的耕地又极其有限,人满为患,过剩人口就必然外溢。江西、福建、安徽、两湖等地区在明清时期均先后出现大量过剩人口,人稠地狭的矛盾日益突出。如江西“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袂接,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比比游食他省”(《海瑞集》上编《兴国八议》);吉安府吉水县“土瘠薄物力无所出,计亩食口仅得十三,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光绪《吉水县志》卷九《风俗》)。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四处流徙。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地土瘠薄,早在明代,迫于人口的压力,其山区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闽中自高地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为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可谓地无遗地矣”(谢肇制《五杂俎》卷四《地部》)。然而相对于剧增的人口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大量人口不得不到他省谋生度日,从而出现“人尚什五游食于外”的情况。安徽安庆县也是清代前期和中期长江流域人口输出中心之一。实际上,明清人口过剩一直是个全国性问题,就连一向被认为垦殖程度较低、人口稀少的两湖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如湖南平江“至明万历时,人满地尽,更无可垦之土”(同治《平江县志》卷十四《赋役》)。到清代更出现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在这种人口形势下,与这些区域相毗邻的浙西山区出现外来移民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浙西山区的开发早在清代以前就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宋代已有梯田,但是在那些陡峭的山坡上,当地的土著依然无法开垦,“查山土高燥多石,不利稻麦,种苎最为相宜。本地乡民未谙其法,有用之土向来概置之无用。兹异省之山民,辟荒芜以收地利,与古者货恶弃地意颇合”(乾隆《长兴县志》卷十),于是善于“凿岗伐岭”的省内外移民纷纷涌入。
而且,战乱与人口迁移亦密切相关。战争的力度及波及范围将制约一个区域的人口增减及地区移迁面积。在1644—1911年间,江浙一带虽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乱,但浙西山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特殊,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真正对浙西山区人口秩序带来巨大影响的战争是19世纪中叶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次战争期间,即使是偏远的山地也不可能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如地处浙西丘陵山区的严州府,便是太平军与清军多次厮杀之地。关于这一地区人口死亡的情形,何炳棣先生在他的书中引用了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观察报告:
“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者造成的。连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难以穿越的灌木林。……无论是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1]284
位于浙西山区其他府州的人口亦是损失惨重。如杭州府之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昌化县,“洪杨之役,由淳窜昌,首当其冲,民气凋残,垂六十余年,未易恢复原状”(民国《昌化县志》卷首);湖州府长兴县,“兵燹之余,民物凋丧,其列于册者孑遗之民仅十之三焉;田赋之入仅十之四焉。故家遗俗十不存五;而城垣桥庙官廨之修复者仅十之三,而颓废者十之七焉”(同治《长兴县志》卷首,光绪元年长兴知县恽思赞《序文》);而在孝丰县,战后户口仅剩三十分之一(光绪《孝丰县志》卷四《户口》)。
由于战争持续时间太长,加之灾荒和饥馑以及同治元年由安徽传播过来的瘟疫,使得浙西人口损失惨重。如湖州孝丰县,“同治元年六七月瘟疫,民遭兵戈者半,遭瘟疫者亦半”(同治《孝丰县志》卷八《祥异志》)。这样,浙西山区人口在战争期间的或死或逃造成了一些府州县出现了人口“真空”或“半真空”的状态,从而引起了此后外地区人口的填补活动。一些地方官也积极招徕客民进行垦种,如严州知府说道:“查严郡各属田地荒芜,人民稀少,较他郡情形,蹂躏更甚。……今欲招垦,必须外来之户乐于耕种。……无如外来垦户,由江西者则有衢之荒田可耕,由宁绍来者则有杭属之荒田可耕,惟严郡居中,止有徽州一路。徽、严交界地方皆系荒产,断不肯舍此适彼。惟查有棚民一项,向来以种山为业,地方农民不与为伍。自咸丰十年后,粤匪滋扰,棚民僻处深山,未受大害,较农民尚胜一筹。昔日无田可种,而不能不种山;今日有田可种,而能改种山为种田,田之出息究胜于山。各棚民非不愿种,实不敢种,须设法招之使种。”(戴槃《定严属垦荒章程并招棚民开垦记》,《皇朝经世文编》卷十)
在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随之涌入。如战后的昌化县,“客民纷纷盘踞,以
四、七都及外五都占大多数,不似他处之纯粹族居”(民国《昌化县志》卷首);临安县,“同治初年兵燹之余,招集流亡,仅存丁口八九千人。三年,劝招开垦,客民四集,自此休养生聚。二十年余年始有丁口土客四万余人”(宣统《临安县志》卷一《风俗•善政》)。
最初来浙西山区开垦荒地的客民是本省人多地少的宁、绍、温、台诸府农民。如余杭县,据光绪《余杭县志稿》记载,各籍移民中,以来自绍兴府的最多,达50.3%,次则宁波和温州,分别占15%和11%,再次则为河南、苏南和本省台州府,分别在4%~6%之间。[2]又如严州府,李希霍芬对战后的移民曾有以下观察:“外来移民已经开始进来了,在分水河谷我发现相当数量的新移民,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但也有少数来自其他省份。”[1]285这些地区农民受战争影响较小,同治三年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提及浙江各地的残破情形时说:“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左宗棠《浙省被灾郡县同治三年应征钱粮分别征蠲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九)
不过,由于浙西杭嘉湖平原地带在战争中受创也重,人口的缺口实在太大,而宁波绍兴等地本身亦在战争中受创,向外输出人口有限,何况一些客民的流动性较大,一俟家乡情况有所好转,常常弃佃返归,致使田地垦而复荒。又因为平原农民不适应山地耕作,所以向山地移民进展缓慢。就在这时,更远的两湖、河南、安徽、江西、福建等省的移民蜂捅而入,“自粤匪乱后,客民垦荒,豫楚最多”,“两湖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同治《湖州府志》卷十八《金其相建玖磬山书院碑略》)。其中就有不少人迁入浙西山区占耕荒旷山田。当时外地客民主要迁入湖州府的西部和南部,时人指出:“郡西山田荒旷尤多,温台人及湖北人咸来占耕。自同治至光绪初,湖北人蔓延郡东。”(民国《南浔志》卷三十)
据此可知,浙西山区的移民活动均属人口稠密的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的流迁模式,即依靠提供空旷的山地来吸纳周边地区的过剩人口,仍然属于向山区要土地,进行农业垦殖的人口流动模式。这与浙江平原地带对过剩人口的吸纳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后者主要是依靠突破原有的经济结构模式即通过非农化的转移来完成的。因此,这些移民的经济活动直接影响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口流动与当地生态环境变化
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状态。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认识程度,人类实践对生态环境的改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生态环境。一个地区生态环境的形成和变迁,除受当地的自然条件影响外,还常常受到人口的负载量和生产配置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因此,清代大量涌入浙西山区的移民及其经济活动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迁往浙西山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耕活动,但并非从事单一的粮食生产(山土高燥多石也不利于种植稻麦),而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他们所种的农作物包括苎麻、靛、落花生、玉米(苞芦)、番薯等。如迁往湖州以西一带山区的温州人,“其人剽悍多力,荷锄成群随垦,结厂栖身。所种山薯或落花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寿昌县,“然如麻、靛两种,亦自近年江闽蓬民有之”(乾隆《寿昌县志》卷一《物产》)。时人张鉴在其《雷塘庵主弟子记》中也说:“浙江各山邑,旧有外省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其中种植玉米与番薯等
杂粮主要是解决自身的口粮,产品进入市场的较少。然而苎麻、靛青、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却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带有明显的商品生产性质。如在安吉,种植苎麻者“自闽人及江右人租乡村旷地设厂开掘而种莳壅既工,获利始倍”(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
在热衷于种植经济作物和杂粮的同时,这些外来移民也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从事筑窑烧炭、砍竹造纸、烧制砖瓦等带有显著山区特色的手工业活动。如炭为安吉山区土产,二三月间,“万家岸、马家渎小市诸处肩卖者络绎不绝”。其中生炭(亦称硬炭)多为徽宁人居此筑窑烧制的。炭又可以用于烧制砖瓦缸甏,安吉北乡烧缸甏者“有百余家,皆宁波人,颇获厚利”。而砖瓦则大多由徽宁江右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以售”(乾隆《安吉州志》卷八《物产》)。竹亦是山区特产,同时竹也是造纸的好原料。在安吉,来自本省的萧山、富阳的移民大多是造纸工匠①。(注:新版《安吉县志》第三编《居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安吉县的社会经济结构》,《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开发的蔓延,浙西山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山区社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和繁荣,生态环境包括生态平衡与土壤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为浙西山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改变了当地山区人烟稀少的面貌。“流民之来益众,则棚益广,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且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居”,“联络盘踞,岁引日多”,“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杂缀》),使大量荒漠的山地得以开垦,而且促进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农副产品通过市场进入了流通领域,丰富了当地农村市场。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有些移民租用或开垦大片土地从事商品性农业垦殖,其间亦多有采用雇佣劳动从事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使山区农村经济结构发生嬗变,在较落后的地区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萌芽。
浙西山区移民的迁入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山区小市镇的发展与繁荣。有些山区小市镇的兴起甚至完全是因为移民的迁入。如长兴县的鸿桥镇,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因战乱流入大量难民应运而生。“阖邑难民及四处商贾,俱麇集于兹。帆樯林立,(缺)尘嚣,俨然一哄之市。”(同治《长兴县志》卷一下《建置汾革•镇市》)虽然这些小市镇仅仅是地方性的小市场,远不及浙江平原地带诸如双林、菱湖、南浔等巨镇的发展,但也颇有自己的特色。如长兴县施渚镇成为山货集散地,“街道宽长,山货骈集,茶笋时尤盛”(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村镇》);武康县的三桥埠是竹木集散地,“舟楫交通,商贾辐辏”;上柏镇,是浙西竹木山货的集散市场,“西南余杭、安(吉)孝(丰)货陆运者,皆出于市。省会郡城操羸者胥来市购焉,而悉达于镇市之河”(乾隆《武康县志》卷八,刘守成《开湘西市河记》)。山区市镇的繁荣又吸引了外地商贾来开店设肆。如施渚镇,清中叶“居民约上千家”,与平原地区部分市镇相比也不逊色(同治《湖州府志》卷二十二《舆地略•村镇》)。昌化的栗树溪市成为“商民聚集,舟楫停泊之所”,白牛桥市“居民稠密,水陆交通”(民国《昌化县志》卷一《疆域》)。安吉的四安镇由于各地商人汇集于此,同治中曾建立新安公所于西门,光绪十七年宁绍商人亦建宁绍会馆于四安南门,以地缘纽带联络乡谊,保护同乡的利益(光绪《长兴志拾遗》卷上《公建》)。
不过,前来开垦浙西山区的移民大多数是自发性的封建流民,他们“聚散无常,往来莫定,其间良顽不一,易於藏奸”(光绪《严州府志》卷之九《食货》)。一些流民性情凶悍,为了生计,往往“强垦人土,或掠人妇女畜产”,扰乱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奸猾时闻”、“斗殴争论之事繁矣”,引起当地官府的惊慌和本地人的痛恨(同治《安吉县志》卷七《风俗》)。
他们来到当地,往往“视土所宜”从事各式生产,是一种盲目的无组织生产活动。据同治《湖州府志》卷九十五载,在山区其垦殖扩张所及,多为“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崇山峻岭,密菁深林”之处,在此类地方进行农业开发,只能是采取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的经营方式。尤其是玉米、番薯等耐旱作物的引种,更使得这种经营方式在山区非常流行,农业经济效益一时似乎显露,但时间稍长,这种盲目性、掠夺式的开发便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
其一,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且松动的山土砂石冲入河流,堵塞水道,淤积下游田地,淤塞河溪、湖泊以及其他水利设施,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在清代方志中多有反映。道光《建德县志》卷二十一《杂记》记载:“近来异地棚民盘踞各源,种植苞芦,为害于水道农田不小。山经开垦,势无不土人松石浮者,每逢骤雨,水势挟沙石而行。大则冲田溃堰,小则断壑填沟,水灾立见,旱又因之。以故年来旱涝濒仍皆原于此。”嘉庆《于潜县志》亦有外来移民垦山种植玉米导致水土流失的记载。此外,在地方官的禁令和上奏的奏折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记载。如嘉庆二年浙江巡抚颜检上了一道奏折,指出棚民“翻掘根株,种植苞芦,以致土石松浮,一遇山水陡发,冲入河流,水道淤塞,濒河堤岸多被冲决,淹浸田禾,大为农人之害”①。[注:《浙江巡抚颜检为遵旨酌议稽查棚民章程事奏折》(嘉庆二年),刊于《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嘉庆六年的《抚宪院禁棚民》也指出,“棚民佃种山地惟苞芦一项,苗壮根长,必须掀松砂土,一经雨水冲激,溪河每致淤积,地方屡受水患”,“山土砂石乘雨流淤下游田地,易起争端,大为目前水利之害”。
其二,造成垦殖之山地物产枯竭,地力尽失。由于客民、棚民来到山区一般都是以租赁的形式从事生产活动,“初至时以重金谄土人赁垦土地,赁之值倍于买值,以三年为期。土人不知其情,往往贪其利。三年期满,棚民又赁垦别山,而故所垦处皆石田不毛矣”,“湖州以西一带山,近皆棚民垦种,尤多植包谷,一孝丰人云,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包谷最耗地力,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山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沈尧《落帆楼杂著》,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八《风俗》)。这种开垦山地,习种杂粮的行为对山地地力和山土极具破坏力。数年之后,所垦山地往往变成不毛之地,很难再恢复山力、地力。
山地的过度垦殖,既损害了原山主的利益,又使下游农民利益遭受惨重损失。因此,生态失衡也加剧了当地土著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矛盾冲突,以致浙西山区一些府州县的土著居民以此为契机,要求政府驱逐外地移民。如于潜县,由于垦山种植玉米引起水土流失,“奉阮大中丞出示严禁,产限驱逐,渐见安辑,然犹有年限未满而延捺如故者”(嘉庆《于潜县志》卷十八《物产》)。建德县也在道光年间了禁止棚民垦山的命令,迫使棚民不得不撤离。而移居长兴县的福建、江西移民是因为擅长种植苎麻才获得了永久居住权。同时,为了将外地人口纳入当地的统治秩序之下,官府对有大量外地人口的府县则“别编棚户,各设棚长,以专约束”(乾隆《建德县志》卷一《方舆》),严厉禁止当地土著居民将山地出租给非“编甲”的远方流民(光绪《淳安县志》卷一《旧序•刘世宁序》)。对有棚户留住的地方,每年年底派员视察,并责成山主田主监督检举,否则一体查办(光绪《严州府志》卷九《食货》)。
三、结语
人口迁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这是因为一定的人口分布受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过程的制约,而人口分布的合理与否又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清代浙西山区接纳了大量区域外移民,这对输出地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日趋紧张的人口压力;对本地区而言,则不仅解决了山区劳动力资源匮乏的难题,又引进了新的作物和新的生产技术,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但是这种自发调整所形成的人口分布并非是合理分布。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有限的山地资源遭到掠夺性的开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诚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结果又取消了。”[3]山区过度垦殖的恶果又激化了土客之间的冲突,外来移民受到驱逐或限制,山区经济的繁荣最终成为昙花一现。
- 上一篇:学校处置突发事件措施方案范文
- 下一篇:税务局农业税及其附加实施方案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