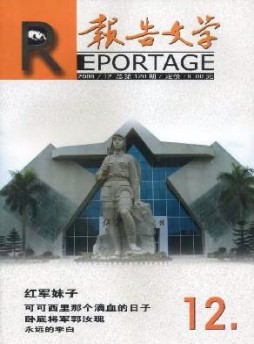文学翻译的辩证观范文
时间:2022-09-11 10:09: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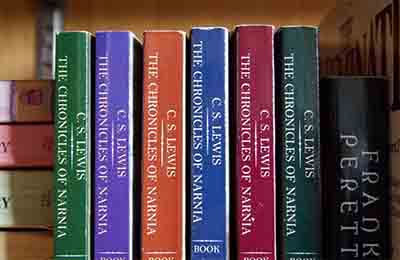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外语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1文学翻译之争的根源
文学翻译之争的根源在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使文学作品具有抗译性,按照语法规则翻译过来的文字常常不具有诗学韵味,犹如一杯芬芳的葡萄美酒变成白开水,甚至是夹杂泥沙的浑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译者时时处处面临选择,正如严复感言:译事三难“信达雅”。“翻译毕竟不是临摹图画或者依样画葫芦,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暗示和精神韵致在另一个文化语境里往往发生变异或流失。”(郑海凌2005:1-2)“希莱尔马诃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们这儿来。”(钱钟书2002:78)“汉化”的翻译,追求译语语言的“文学性”;“欧化”的翻译,追求译语语言的“忠实性”。诗化的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根本因素,雅各布森以此为基础提出“文学性”的概念,意在强调文学作品的语言生动、优美,富有感染力(Якобсон1921:11)。文学翻译研究中所说的“文学性”指译语须是诗化的语言,要有文采。“忠实性”指译语要追随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性和忠实性构成文学翻译的主要矛盾,是千百年来围绕文学翻译所形成的文质之争、直译意译之争和归化异化之争的实质性概括。既能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又能妙笔生花,文采飞扬,当然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但是,语言文化差异性客观存在,造就文学语篇的“抗译性”,在与“抗译性”的博弈中彰显出译者的功夫。如果文学性与忠实性不能兼得,译者该何去何从呢?是坚持文学性第一,还是忠实性第一?
2语言功能与语篇翻译
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语言功能”的定义是:(1)语言形式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能力;(2)在语言系统所有层级中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布拉格学派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提纲》提出对语言进行功能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由于执行不同的社会功能、用于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因而划分出不同的功能类别。(张会森2002:88)但是在韩礼德(Halliday)之前的学者大都没有把语言功能与语言结构本身联系起来,而是着眼于语言的不同用途。在韩礼德看来,语言功能不只体现在不同的用途中,而首先是体现于语言系统,尤其是语义系统的内部结构中(周晓康1988:20-25)。韩礼德(1985)指出,任何语篇都是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构建体,同时体现3层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韩礼德的语言元功能概念与语言结构分析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对语言解释有着更强的说服力。由此我们认为,目的语语篇和源语语篇一样,同时体现这3种意义。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3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胡壮麟等2005:366)。然而,这种对等是相对的,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测度(陈忠华1990:8-11)。在具体语言转换过程中,两种语言的语篇会有一些变化。
语言的外部功能是其社会功能,制约其内部功能,语言的内部功能服务于其外部社会功能,外部社会功能依靠内部功能来体现。例如,科技语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传播科技信息,因此在科技语篇中,语言的概念功能上升为主要的内部功能,表现为在语义系统尽量突出“客观性”,排除人的情感、好恶和个人见解等对事物认识的影响。科技语篇要求表意精确、抽象概括、逻辑严密,为此须要选用大量科学术语、抽象词语和严谨完整的句子结构以及表达各种逻辑关系的语言手段。新闻语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把有报道价值的事件尽快报道出来,向大众提供信息和力图影响读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新闻语篇的语言具有如下特点:从概念意义上讲,内容广泛,可以涉及所有的语域;从人际意义上讲,表义直截了当,不提倡拐弯抹角,具有表义清晰的特点;从语篇意义上讲,由于讲求时效性,因而篇幅有限,具有意义浓缩的特点。法律语篇的社会功能是向公众提供为保障人类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须遵守的规约和规范,超越这些规定是违法行为,这就是法律语言的人际功能。由于法律语言的特殊社会功能,它不仅向人们表明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必须避免漏洞,防止有意曲解和钻空子,因此法律语言必须词义准确、组织严密。它不求蕴涵丰富、风格优美,只求准确严密,这就是法律语言的语篇功能。文学语篇的社会功能是作家通过塑造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描绘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在给人以美的感受的同时感染读者。为此须要充分利用各种描绘具体形象的语言手段,如各种表示具体事物、动作、特征的词汇、同义词,各种富有表现力的语音、句法手段。语言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具有无限可能性。语言结构是在交际过程中根据其使用功能发展而来,也就是说语篇的社会功能制约其语言形式的选择。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是依据不同领域交际任务的特点和功能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逐渐形成多套分别同社会活动领域相应的、各具特色的言语表达方式,这就是标准语的功能变体。
3文学翻译的原则
文学翻译讲求语言的文学性,用俄罗斯形式学派的话说就是要使用“诗化的语言”。但是,文学翻译并非是林纾式的“美言修辞”,还要注意译文的忠实性。讲求忠实性并不意味着解构主义者和纳博科夫式的反对译文通顺的“悔言修辞”。忠实性应以不违背译语表达习惯,不超过译文读者接受能力为限。文学翻译的艺术永无止境,优秀的译者既能写出精妙的译语,又不无故抛弃原文字句。
3.1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当今语言科学的发展使翻译研究摆脱主观感悟的范式,走上科学化道路。“语言的社会功能决定其形式选择”,文学语篇的社会功能决定文学翻译采用何种语言表达方式。文学语篇的主要社会功能是欣赏功能、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而后两个功能的实现必须借助于欣赏功能。这也说明“文学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性。文学性是作品透过艺术形式流露出的精神气质,是审美愉悦的最初源泉。缺少文学性就像一个人没睡醒,昏昏沉沉无精打采。语篇的修辞手法有两大类:“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消极修辞”只要把话说得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就行;“积极修辞”除了也要求具备这些条件外,还要求积极地随情应景,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使所说所写的事物呈现出具体形象,产生新鲜活泼的动人力量。文学语篇须运用“积极修辞”的手法,使读者产生可触可摸的立体形象,进而接受蕴藏于其中的思想感情。因此,当然得格外讲究语言功夫。高尔基说:“文学创作的技巧,首先在于研究语言,因为语言是一切著作、特别是文学作品的基本材料”。文学译作的社会功能和原作一样,必须具备文学语篇的所有特征,必须使用文学语言。译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新的文学语篇,正是因为它的语言。这是一种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殊的语言———“诗化的语言”。“诗化的语言”既然是构成文学语篇文学性的根本因素,那么,我们衡量一个译本的价值就离不开它的语言和文学性。对于翻译中“文学性”的重要性,译者们早有觉察,我国汉末佛经翻译者中的文派的依据是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六朝高僧鸠摩罗什发现“改梵为秦,失其藻蔚,如嚼饭喂人,非但无味且作呕”。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的西塞罗提倡“演说家的翻译”,主张翻译的语言求美,要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要能打动读者。现代译者对文学翻译的“文学性”的认识更为深刻:郭沫若一直“主张以严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究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郭沫若1984:20)。此外,楚克夫斯基(К.И.Чуковский)、加切奇拉泽(Г.Р.Гачечиладзе)、傅雷、钱钟书和许渊冲等学者无不强调翻译中文学性的重要性。译作具有文学性,才能吸引读者阅读,原作的高尚的道德思想价值和文化交流价值才有可能不被埋没。
3.2文学翻译的忠实性文学翻译讲究语言的美学功能,但是,万事都有“度”的限制,否则过犹不及。如果为了突出译文的文学性,随意裁剪原作字句,甚至添加原作没有的东西,那么翻译则变成东鳞西爪的写作。一些译者为突出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在原作修辞不如意之处对其润色、甚至删节和改写。林纾的翻译就属这类,“林纾认为原文美中不足,这里补充一下,那里润饰一下,因而语言更具体,情景更活泼,整个描述笔酣墨饱……他在翻译时,碰到他认为是原作的若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2002:87)。林纾的现象并非个案,不独中国有之。17-18世纪的法国译风以饰文、纠正原文为荣。18世纪的俄罗斯任意处理原作的做法司空见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罗斯译坛“改写”、“使之适应我们的习惯”成为一种翻译倾向。这一时期的知名翻译家茹科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在俄罗斯翻译史上地位比较特殊,他的大量文学遗产一直让研究者破费猜测:在这份遗产里翻译和原创孰多孰少?莱蒙托夫、普希金的翻译作品也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作进行删节、改写、重构。(吴克礼2006:40)这类翻译侧重译文的文学欣赏功能,文字精美,可读性很强。“钱钟书先生对林译持基本肯定的态度。钱先生以一个文学大师的身份来研究林译小说,拿后来出版的比较‘忠实’的译本与林译作比较,发现林译‘还没有丧失吸引力’,相比之下,虽然林译里‘漏译误译随处都是’,但钱先生觉得许多林译小说都‘值得重读’,而读了那些所谓‘忠实’的译本,‘就觉得宁可读原文’。”(钱钟书2002)这是因为译文首先实现欣赏功能,而后才能实现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林纾翻译的《迦茵小传》和《茶花女》能促使中国封建伦理文化发生革命的原因之一。林纾式的翻译可称之为“美言修辞”,然而这种译文已完成历史使命,在当今时代已不再受欢迎。
文学作品的欣赏功能和教化功能、文化交流功能的辩证关系决定译者在翻译时,要使用诗化的语言,坚持文学性第一。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弃翻译的忠实性,置原文内容于不顾。文学翻译是二度创作,译者必须忠实于作者,这不仅是翻译的天生的属性,还是译者的职业道德。但是,“忠实”同样有“度”的问题,应以不违背译语语言习惯和读者的理解能力为限。超过这个“度”,直译就变成死译、硬译,译文不是语言而是咒语。解构主义翻译观反对译文通顺,目的在于阐明他们的语言哲学思想———不同民族的语言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如果我们在翻译实践中执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那么我们就满足上帝变乱人类语言使他们互相不理解的心愿。翻译失去存在的价值,翻译已被解构掉。纳博科夫的翻译观与解构主义者的翻译观不谋而合。身为作家的纳博科夫是一位极端的直译者。纳博科夫在翻译实践中身体力行自己的翻译观,结果发现直译(他主张的直译其实应该叫做死译、硬译)行不通。在用英语翻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纳博科夫意识到极端的逐词翻译无法曲尽原意,因此主张依靠注释和评论来阐释。他甚至主张注释的篇幅可以超过译文本身的长度。纳博科夫翻译的《奥涅金》共4卷,1200页,译文仅占228页,其余均为详细的注释和评论。(许钧2000:257-258)纳博科夫坚持直译是一种策略,以此说明翻译是不可能的,而不是要通过直译译出原作的精神实质。(许钧2000:261)评论家托马斯•肖说,“纳博科夫自己的散文……往往像地地道道的诗,而他的《奥涅金》的诗体翻译连散文也算不上”(Shaw1965:113)。
有人对纳博科夫的翻译冠以“学术翻译”的雅称,尽管纳博科夫本人并未对译作的社会功能进行界定,他的翻译目的并不是进行学术型翻译,而是个人翻译观使然。纳博科夫翻译的《奥涅金》本身算不上文学作品,但客观评价而言,这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译文本身,而在于纳博科夫所做的大量注释和评论产生的学术价值,这些注释和评论为研究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提供大量素材。从这一点上讲,这是一部学术性极高的译作。因此,“一般来说,译者当然很难苟同纳博科夫关于译作要加大量注释的这种极端观点。但在需要一个权威文本时,加注是十分必要的……纳博科夫《奥涅金》的译本是一部标准的学术翻译的典型文本”(Shaw1965:121)。其实,纳博科夫的译本与其说是“翻译”,不如称作“注解”更合适。纳博科夫式翻译与原作亦步亦趋,字比句次,这样的译文貌似忠实于原作,实则貌合神离。无数翻译实践证明,逐词翻译、与原作保持形式对等永远不可能正确。这样的译本文学性不强,可读性不佳,意义模糊、晦涩,难以理解,读者即使有巨大的耐性也无法读下去。由此想到《季羡林谈翻译》一书中季先生回忆上世纪50年代读卢那察尔斯基文艺理论时的情景,“痛苦不堪,彻夜失眠,译文晦涩难懂,读了两章再也无法硬着头皮读下去”,虽然译者淳淳教导读者一定坚持读下去,里面有宝山,可季先生说“宁可舍弃宝山也不愿读了”(季羡林2007:9)。遇到晦涩的译文,虽然译文内容很重要,季先生尚且如此感受,何况一般的读者呢,文学本是生活的佐料,没有也罢,如果语言生硬晦涩的话,读者更容易放弃。朱光潜说过,“世间有许多高深的思想都埋没在艰晦的文字里,对于文学与文化都是很大的损失”(朱光潜2004:94)。厚厚的《鲁迅全集》里翻译部分占一半以上,可是除翻译研究者外,有几个读者愿意读鲁迅先生那些欧化味很浓的译文呢?我们这里且不论鲁迅先生的“宁信而不顺”翻译观的历史成因。对比语言学研究成果表明,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语法、自己约定成俗的修辞手段和自己惯用的表达方式,而这一切不可能用相应的词汇译成另一种语言。译文紧跟原文,语言必然笨重凝滞,反倒距离原文最远,因为原文的语言是艺术的语言,是吸引读者的语言,而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因为读者往往把译文风格当作原文的风格。“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钱钟书1979:101)这样的翻译不是延长原作的寿命,而是替作者决绝读者。不少笨重凝滞的译文是译者受传统“信”的翻译观念影响无意识而为的。
而纳博科夫式的翻译则是译者有意而为。这类译者不是不懂得文学作品语言的艺术性,不是不懂得读者的接受心理,而是个人独特的翻译观使然。译文的主要对象是看不懂原著的人,而不是为学术研究而翻译。纵观世界翻译史,几乎找不到一个单纯为学术研究而翻译的译者。译者的工作不应该是为看得懂原著的评论家提供评论他所译的某一语句是否忠实,不是为翻译研究者提供比较素材,不是为语言研究者提供比较语言差异性的机会,也不是为文化研究者提供文献,而应该是为广大读者提供美仑美奂的文学作品,启发他们的心智。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得翻译的“忠实性”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字比句次地逐词精确,这样的译文与原文貌合神离,反而距离原文更远。“忠实”作为翻译天生的属性和译者的职业道德,要求译者最大限度保留原作语言形式,但这要以不违背译语遣词造句习惯和不超过读者接受能力为限。
3.3文学性和忠实性的辩证统一文学翻译要讲求译作的文学性。坚持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并不是说译者可以天马行空脱离原作随意泼墨,坚持文学翻译的文学性要警惕林纾式的“美言修辞”。文学性以忠实性为基础,“忠实性”并不是死译硬译,我们反对纳博科夫式的“悔言修辞”。优秀的译作应是文学性和忠实性的辩证统一。文学性与忠实性是天平的两端,译者如何调节天平的平衡呢?一方面应避免死译硬译,为此译者应自觉地抵制源语语法的干扰,应按译语遣词造句习惯重新排列句子,不生拉硬拽,弄出一堆看着刺眼读着拗口的欧化汉语,获得解缚去感。翻译过程中的死译和硬译往往是因为译者易被外文语法牵着鼻子走,翻译出洋腔洋调的中文,对付这种现象,思果形象地说,“原文放在译者面前,好像狱卒,好像桎梏,好像神话中诱惑男子的妖女,使译者失去自由,听其摆布,受其引诱。为避免英文语法干扰,做翻译的人要拳打脚踢,要保持甚至清醒,意志坚定,才能自由”(思果2000:6)。另一方面,译文还要最大限度保留原作句法形式,特别是那些具有前景化效果的句法结构。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文学翻译不是文字翻译,而是忠实于原作风格的翻译,文学的语言风格与句法结构有直接关系。译文要再现原作的风格,除了追随原作的句法结构之外,别无他法。按照汉语遣词造句习惯重新排列句子与保留原作句法形式是一对矛盾。但是文学翻译是一项永无止境的艺术,优秀的译者能因难见真功,巧妙地化解这一矛盾。即使因语言的差异性实在不能化解这个矛盾,也能以得补失,采取补偿办法使原作句子的艺术表现力在译文中再现,“翻译不像洗一件衬衫,可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翻译像琢玉,可以琢磨个没完”(思果2000:30)。
“思想感情与语言是一致的,相随而变的,一个意思只有一个精确的说法,换一个说法,意味就完全不同。所以想尽量表达原文的意思,必须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组织。”(朱光潜2004:121)译文不仅字字珠玑,而且和原作亦步亦趋、文从字顺,这是每个译者的愿望。但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这个愿望的实现很不容易,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严谨的译者呕心沥血在两种语言中寻找最佳契合点,尽可能最大限度保持原文语法结构,译文语言贴切而不刻板,有长句而不欧化,自然流畅。这种译法很吃功夫,译者须经多年摸打滚爬的翻译实践才能练就。思果根据自己丰富的翻译经验,总结出“外文中的大部分句子,可以照原文词序翻译,办法是改变连接词,或补充一些无关紧要的字句。译不妥的地方,再加以适当调整。这样译的好处是译文自然易读、快、明白、省事、顾全语境、情绪”(思果2001:29-31)。例如:①...Takeawordofadvice,evenfromthreefootnoth-ing.Trynottoassociatebodilydefectswithmental,mygoodfriend,exceptforasolidreason./……听我奉劝你一句话,别管我是个三英尺高、不值一文的人。不要把身体的缺陷和头脑的缺陷,混为一谈,老兄,你如果有充足的理由,自然又当别论。例①有很大的抗译性,特别是evenfromthreefootnothing和exceptforasolidreason这两个介词短语作独立成分而形成的小句,但经过思果的匠心独运,这段译文不仅是生动地道的汉语,而且保留原文的句法结构和语序,堪称妙译。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文学性以忠实性为基础。脱离原作的文学性,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翻译活动的范畴。理想的译文语言是“亲切的母语中带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像扑面的晨风给人以清新的愉悦”,“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者努力消除两种语言之间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牵强的痕迹,使译语的生成尽可能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郑海凌2005:67)。
4结束语
文学翻译是美与信的问题,尽管争论了近两千年,但至今没有定论。文学语篇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只有被读者阅读,这些重要功能才能得以实现。译文读者喜爱读的文学译作必定文辞精美、富有感染力,这意味着文学翻译的欣赏功能是实现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的前提。因此,文学翻译首先要具有文学性。但是,翻译天生的忠实性和译者的职业道德要求文学翻译不能是林纾式的“美言修辞”。同时,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翻译的“忠实性”并非纳博科夫式字比句次的“悔言修辞”。文学翻译是文学性和忠实性的辩证统一。
作者:徐红 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
- 上一篇:《看护学教程》译者介入的困境范文
- 下一篇: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范文
精品推荐
- 1文学与文化论文
- 2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 3文学专业论文
- 4文学价值论文
- 5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 6文学作品分析论文
- 7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利与弊
- 8文学作品论文
- 9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 10文学写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