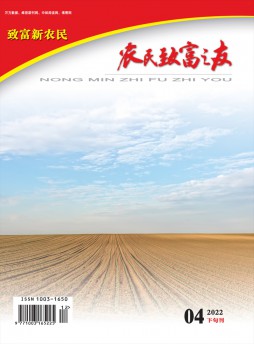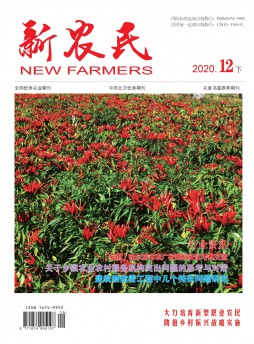农民政治参与及社会效应范文

直接、公开、竞争的村民选举制度导入中国农村社会以后,如何认识和评判农民政治参与的社会程度、动机与效应?根据现有文献,无论是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及动机的分析,还是对农民政治参与效应的评估,都以基于个案观察或者政策文本所进行的定性分析为主。根据地方性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研究的,主要有何包钢、郎友兴在浙江省完成的1245份问卷调查(何包钢、郎友兴,2002年);刘喜堂、贺雪峰1999年对湖南40个县的村委会选举数据分析(贺雪峰,2000;刘喜堂,2001);谢子平、吴淼对福建2000年村委会选举调查数据分析(谢子平,2001;吴淼,2002);孙龙、仝志辉对吉林省40个村委会选举的数据分析(孙龙、仝志辉,2002);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等对江西40个村的宗族与村治关系的调查研究(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2001)。
上述调查的分析单位主要是村组织而不是村民个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村委会选举制度及其相关因素而不是村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研究的角度主要是研究者对农民政治参与过程及效应的描述和评价,而不是农民自身对政治参与及其效应的自我评判。笔者的研究则以村民个人为分析单位,并根据参与者的自我评判来分析他们的政治参与动机、价值取向及参与效应。为此,笔者于2002年5-6月组织了在广东全省范围内的问卷调查。①调查活动在广东省26个村展开,每村平均访问了70个村民,共回收有效问卷1852份,有效率926%。调查地点的选择主要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梯度特征,将被调查村分作三大类:一是珠江三角洲中心区域的农村,具体包括广州市白云区、花都区及从化市,佛山市南海区、东莞市、鹤山市的10个村;二是珠江三角洲边缘区域农村,包括肇庆地区的云浮市、阳春市、郁南市的8个村;三是分布在粤东及粤北山区(潮安县、五华县、兴宁市等)的8个相对落后的村。从总体上看,珠江三角洲与非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农村经济差距很大,富裕农村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贫困农村主要分布在粤北山区及各地的石灰岩地带。东西两翼部分市县如惠来、陆丰、廉江、雷州等地贫困村的发生率也不低。①根据我们的调查数据,1704个被访者(缺失148人)的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是5455元,标准差为740839元,离差系数达0.74,表明被访者的经济收入悬殊不小。按被调查者的年人均收入分组②:贫困户占289%;温饱户占271%;小康户占212%;富裕户占227%。
为把握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特征,本文首先从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区分了过去的农民政治卷入与当代的农民政治参与的不同,描述了体现公民赋权的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及参与的实际程度。接着,分析了农民参与选举的权利动机和价值取向,而这种参与动机、价值取向以及农民的制度性支持程度,同其对村民选举的制度绩效及社会效应的自我评判有内在的关联,揭示这种关联性正是本文的基本目的。
一、转型中的农民政治参与
无论我们如何评估以村民选举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的政治效应,直接、公开、竞争的村民选举无疑是一种公民赋权(empowermentforcitizenry)行动。公民赋权并不是国家授权给公民,而是公民政治权利获得制度化实现渠道的宪政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
回顾1949-1979年的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群众性政治运动从未间断过,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浪潮把亿万农民席卷进去。笔者将这种卷入式的政治参与界定为“政治卷入”(politicalinvolvement)。政治卷入是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形态③,它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人治取向。这种政治卷入是以人治为特征的自上而下的群众运动,是农民群众响应国家特别是最高领袖政治号召的社会行动,而不是基于自身经济利益要求及政治权利主张的积极行动。第二,工具主义。这种政治卷入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缺乏个人选择机会的被动行为。卷入政治运动的农民,由于缺乏政治或政策选择的机会,往往成为服务和服从于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或者成为无自主意识的政治盲从者。第三,阶级斗争。这种政治卷入其实是群众性阶级斗争运动。参与者不是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地位参与公共生活,而是以家庭的阶级成分来划分斗争者与被斗争者。它给社会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在于,尽管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成了事实上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他们的政治权利也被无限期地剥夺了,中国社会就是在“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的人为分割中断裂了。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卷入,实质上是国家通过阶级斗争而实现的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控制。有学者认为,时代是让那些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贫下中农去决定国家的命运,后来则是让农民自己学会决定自己的命运(周晓虹,2000)。这个判断不无深刻。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把农民当作社会的主体阶级来对待,最多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已。在政治上,中国农民的这种非主体定性、受支配地位,不会因为少数从农村社会脱颖而出的政治活动家(如陈永贵)而改变。无论农民卷入“群众批斗”,还是参与“民主办社”,都是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政治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公民赋权运动首先在农村社会登陆,导致农民政治参与的形态、动机及效应发生根本的变化。有研究者认为,80年代以后(所谓“后时代”)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不是过去的自然延伸,而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体现(周晓虹,2000:146)。然而,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突出特征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抗争性参与,具体形式有如农民依政策抗争(policybasedresistance)或依法抗争(lawbasedresistance)(Li,Lianjiang&O’Brien,1996:28-61;李连江,1997)、非制度性参与(程同顺,2000)和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郭正林,2001)。当然,制度化的选举投票活动是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渠道。
①②③笔者不认为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就没有自主性。决定参与自主性的关键因素不是“动员”,而是在参与过程中的选择机会。如果参与者缺乏选择的机会,那就是笔者所界定的“政治卷入”。按照广东省确定的农村小康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为贫困农村,2000-4000元为温饱型农村,4000-6000元为小康农村,6000元以上的为富裕农村。2001年广东全省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是3770元。参见广东省农村调查队:广东农村贫困今年略见缓和,见2002年12月23日广东农村经济信息网(http:www.agri.dg.gov.cn)。
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和投票,如县乡人大代表、村民代表选举、村委会选举,党支部选举、党支部候选人推选投票等等。制度性参与还包括参加村民会议,听取及表决村委会工作报告,与各级干部联系和接触等。中国农村制度性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程度的提高,是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提高的体现。非制度化参与则包括集体上访告状、依法或依政策抗争、公共场所的群体骚乱以及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报复性攻击等。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普遍面临的干群关系紧张局面,表明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面临严峻挑战。程同顺的研究也表明,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趋势,非制度化参与、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并存在合流的趋势(程同顺,2000:253)。这些经验现象表明,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不再是单纯的服从性参与,开始从过去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具有权利主张的政治参与形态。由此,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呈现出制度性、权利性和自主性等多重特征。
我们的问卷调查设计了衡量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变量,主要是农民参与村委会、党支部和人大代表选举的频度。我们将被访者分成“中共党员”和“普通群众”两大群体(其中党员占182%;非党群众占818%,缺失108人)。他们参与村委会选举的次数如表1所示。
表1参加村委会选举次数选举次数政治面貌参加村委会选举次数(%)1次2次3次多次没参加频次党员2554269149179329群众18346261422521415总计19745567442381744表1显示,在党员和群众中,分别有179%和252%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选举。综合来看有238%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村委会投票活动,表明村委会选举的参选率与官方所公布的参选率数据存在差距。①经相关分析,政治面貌指标同参与村委会选举次数相关的Gamma系数(以下简称“G系数”)为0073(显著度为0119),表明两者基本上不相关。但是,政治面貌同个人的竞选动机呈中度相关。在“是否想竞选成为村委会主任或村委成员”问题的回答中,“政治面貌”之间的G系数为062,显著度为0000。性别、年龄、收入水平同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相关程度都不高,G系数分别为0036、0115、0077,显著度均低于0005。表2参加党支部选举次数选举次数政治面貌参加党支部选举次数(%)1次2次3次多次没参加频次党员17624010397383329群众231811069421415总计526029248371744表3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次数选举次数政治面貌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次数(%)1次2次3次多次没参加频次党员24621910070365329群众8613652237041415总计11615161326401744表2反映的是党支部选举情况。“党支部选举”既包括党支部内部选举,也包括村民群众推荐党支部候选人,即所谓“两推一选”或“两票制”的选举参与。先看“群众”这一栏,有942%的被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党支部选举,这表明被访的普通农民并没有真正参与“两票制”或“两推一选”的政治活动,而许多地方官员声称开展了这项重大的改革。其次,看“党员”这一栏,调查结果显示有383%的党员被访者没有参加过党支部选举,表明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还没有达到应有水平。G系数分析结果,政治面貌同党支部选举参与程度呈高度相关,其他变量按照相关程度高低排列依次为:性别、年龄、人均收入和职务经历。
①据民政部召开的全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情况分析会(2002年11月21-25日,宁波)透露,2002年村委会选举中,广东省的参选率为96%;海南省的参选率为956%;四川省的参选率为9346%,选民亲自投票率为7788%;湖南省的参选率为9151%。江苏、四川、新疆等地选举一次成功的村占到总数的90%以上。
选举县乡人大代表是农民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制度渠道。表3是问卷统计结果,由此可见,党员参加县乡人大代表选举的机会比非党员要高。有1次选举经历的,党员是非党员的3倍;2-3次经历的为2倍左右,多次经历的是3倍多。而非党员被访者中没有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的是党员的2倍。就参与人大代表选举的状况来看,统计分析发现个人的政治身份同政治参与的相关明显,同人均收入基本不相关。为综合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笔者将相关数据综合成表4。表4影响农民政治参与因素的综合分析因素参与程度性别(GSig)年龄(GSig)经济收入(GSig)政治面貌(GSig)职务经历(GSig)村委会选举0185000003500000007700110073011902030000党支部选举0367000001640000001507390894000006540000人大代表选举0113000701110000003702320479000003360000综合测评0222-0208-0043-0482-0398-表4显示,影响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年龄和职务经历;对党支部选举的参与而言,显著的影响因素是个人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而影响人大代表选举参与的主要因素也是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从因素分析来看,年龄因素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最强,性别因素对党支部选举的影响最显著,经济收入对人大代表选举有微弱影响,政治面貌对党支部选举的影响最强,职务经历也主要是影响党支部选举。综合测评的结果显示,经济收入对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弱(G系数为0043),政治面貌和职务经历的影响比较显著(G系数分别为0482和0398),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影响程度属于低度相关(G系数分别为0208和0222)。由此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同个人收入水平几乎不相关,而同个人的社会政治面貌及社会身份(通过职务经历来体现)关系密切。
二、政治参与的动机与取向
农民在政治参与中有没有明确的动机?大部分学者肯定,农民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寻求经济利益保护的机制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和动机。例如,徐勇认为支配和影响村民选举的因素主要是利益机制,而驱动村民政治参与的利益,既包括集体公利、小团体共利,也包括个人私利(徐勇,1999:298-299)。何包钢、朗友兴的研究发现,经济发达村要比经济落后村的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高,选民对投票回报或选举的误工补贴的期望是村民高参选的重要因素(何包纲、朗友兴,2002:163-165)。胡荣的案例研究强调农村选民的经济理性选择,其研究也发现村民参选的回报和候选人竞选的经济利益计算是农民参选的主要动机(胡荣,2001:57、100)。程同顺则强调农民经济利益对政治参与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和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和表达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更多地参与政治。国外学者也从经济发展与民主参与关系的角度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动机问题(Oi,1996;Oi&Rozelle,2000;Shi,1999)。
从非经济因素来探讨农民政治参与,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例如,于建嵘在湖南的田野调查支持这样的结论:农民公共参与(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是目标非经济化和自愿不足。参加选举的农民并不认为选举投票对他们的自身利益很重要,他们寻求的是“做事公道”(于建嵘,2001:415)。何包纲和郎友兴的实证调查则显示,农村选民的投票行动主要受其政治权利及公民责任意识驱使,表明农村社会的公民意识正在形成(何包纲、郎友兴,2002)。周晓虹则从自上而下的视野,认为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动机主要是破旧立新,以后的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主要是制度重建及制度创新(周晓虹,2000)。国外学者中,欧博文和李连江对农民政治文化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他们的研究发现,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O’Brien&Li,1996;欧博文,2001)。不难看到,农民的公民权利意识在觉醒之中,成为捍卫其选举与被选举权的动力来源。
综合来看,开启于20世纪80年代非集体化改革的中国农村政治参与,得益于村民直选、村民自治的制度实施,正在从过去那种工具性的群众政治卷入转变到权利性的公民政治参与。然而,这种政治转型还远未完成,农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力及动机,究竟来自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还是经济利益的寻求,有待后续的研究加以回答。
(一)农民的选举动机
本调查设计了五个变量来测量被访者的选举动机与取向。第一是调查了解被访者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以及参加选举的主观愿望;第二是对当选村干部(包括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第三是选举投票误工补贴对选举参与的影响。我们假设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与其公共参与的程度有相关。为此,我们首先看一看被访者的公共意识结构。表5显示了1852名被访者对村庄公共事务关心的程度。表5农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村集体财务计生指标分配宅基地使用集体分红农村治安村企业经营关心454260281401615250不关心546740719599385750由表5可见,在所列公共事务当中,被访者最关心的是农村治安,有615%的被访者回答关心农村治安状况;其次是村集体财务和集体分红,关心程度分别为454%和401%。关注较少的是村企业经营及计划生育指标分配,不关心的人数分别高达75%和74%。经G系数分析,对集体分红的关心同村委会选举的参与程度有显著的低度相关(G系数为0217),而其他关心变项与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相关系数G都小于001。我们的假设被证伪了。表6显示了被访者竞选村委会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的愿望情况。表6村民竞选村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的愿望参选愿望政治面貌是否想竞选村主任或村委其他成员(%)想不想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频次党员614247139324群众2293524191396总计3013333661720从表6可见,党员有竞选动机的大约高出群众近2倍,而从没考虑这个问题的群众人数是党员的2倍多,明确表示“不想”的群众也比党员多10个百分点。G系数分析表明,个人竞选动机与其政治面貌的相关系数为0616(显著度0000),与个人职务及人生经历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45(显著度0000)。下面,让我们看一看投票误工补贴对农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刺激作用。正如胡荣在福建观察到的情况一样,广东不少农村也给每个选民金额不等的投票误工补贴。表7是1852个被访者投票误工补贴的分组统计结果。从表7可见,有411%的被访者所处村庄是不发误工补贴的,发误工补贴的占了589%,误工补贴的众数区间是6-10元,平均值为86元。误工补贴同村委会选举参与程度的G相关系数为0256(显著度0000),即统计上的中低度相关。表8显示了误工补贴对村民参加投票选举的经济刺激作用。当问到是否“不发误工补贴村民就不愿意投票”时,195%的被访者明确回答“是这样”,598%的村民表示“不是这样”,还有20%多被访者不置可否。经G系数分析,经济刺激对参选程度的影响不高,相关系数为018(0000)。但同选举的难易程度呈中低度相关(G系数为030,显著度0000)。笔者的分析表明,类似投票误工补贴的经济刺激,不再是激发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而是个人政治觉悟以及人生社会经历。可以预见,一旦农民的公民意识成熟起来,就会增强其政治参与的自主性和权利动机。表7每次村委会选举投票的误工补贴频次与百分比金额(元)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无补贴7624114111-53621951956-1044023823811-2019410510520以上945151总计1852100100表8不发误工补贴村民愿否来投票频次与百分比选项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是这样357193195不是这样1097592598说不清楚380205207合计1834990100缺省值1810-总计1852100-
(二)农民在选举中的政治取向
在投票选举中,农民最心仪什么样的人?这涉及到农民的政治评判与选票投向问题。何包纲、郎友兴的浙江农村调查研究区分出了“能人”、“好人”和“自家人”三类交叉影响的取向,浙江农民的选举取向主要是经济能人(何包纲、郎友兴,2002:213-214)。笔者的调查则细分出七种取向让被访者选择。调查统计结果如表9所示。表9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党员敢为村民说话经济能人办事公道人品好,不贪污有文化,明道理自家人选择19755235179074563165不选择803448649210255369934N=1852人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取向中,排在首位的是“办事公道”和“人品好,不贪污”,这表明农民有很强的公平要求和正义诉求;排在第二位是“有文化、明道理”和“敢为村民说话”,表明农民十分看重知识文化以及敢为平民利益鼓与吹的“包公精神”;排的第三位的是经济能人,这似乎与广东农村的实际情况不相匹配。其实,广东农村的经济能人大多在村外发展,他们给村民带来的实惠并不直接,特别是在非集体化和市场化的现时期,发家致富主要是各家各户的私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民的选举取向中,党员排在倒数第一,仅有不到20%的人选择“党员”。而选择“自家人”的更少,表明广东农民在文化观念上走出了家族影响的阴影。表10党员与群众对选择党员做村干部的态度取向选项政治面貌应该选党员做村干部(%)是不是频次党员359641329群众1638371413总计2008001742调查显示,党员与群众在选择党员做村干部的态度取向上有明显分歧。表10显示,党员选“党员”的比群众选“党员”多了近1倍的人,而不选党员的群众比党员多了近20个百分点。农民的政治面貌与农民这种政治取向的G系数为0482(显著度0000)。由此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党员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政治地位?笔者的调查还显示,在1800多个被访者中,认为“三个代表”给农村带来显著效果的人数并不多(参见表11)。从表11可见,几乎有50%的被访者不知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更谈不上了解其宣传贯彻的效果。在知道“三个代表”的被访者中,认为“效果一般”的人(341%)是“效果很好”的2倍多。
三、政治参与中的农民评判
在此强调的“政治参与中的农民评判”,指的是由农民自己来评价村民选举及其实际效果。
(一)选举还是任命
有的人认为,农民的文化素质低,又没有经过民主启蒙,所以对干部产生方式的好坏缺乏判断能力,即所谓“给钱给物给政策,不如给个好支书”。本调查显示,农民是有政治判断力的。问卷上有个提问:“你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村民选举还是上级任命?”回答如表12所示。表11农村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的效果频次与百分比选项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效果很大290157158效果一般626338341不知道有没有效果345186188不知道“三个代表”指什么575310313合计1836991100缺失1609-总计1852100-表12您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选举还是任命频次与百分比选项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应该村民选举1178636646应该上级任命185100101两种办法都行295159162不知道1658991合计1823984100缺失2916-总计1852100-由表12可见,646%的被访者支持村民选举制度,认为村干部应该由村民选举产生。然而,也有10%的被访者不看好选举制度,认为村干部应该由上级任命。还有16%的被访者是“两可派”,既认同选举制度,也接受任命制度。而在“两可派”中,认为选举无用的人占了很大的比重(参见表17)。表13显示了农民的权威认同结构同村干部产生方式评价之间的关系。经测算,农民的权威认同与对干部选任方式的评价为中低度相关(G系数为025,显著度0000)。从表13可见,在农民权威认同结构中,以“村支书”、“村主任”、“村民代表”为权威认同对象的村民,主张村干部选举制的人数高达70%左右,表明那些认同体制内权威的农民倾向于接受选举制度。而那些倾向于认同体制外权威(如有钱人、大姓族老)的农民反倒接受任命机制,“两可派”、“不知道者”大多也属于这种政治认同。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一般的民主理论都假设私人经济、民间权威与民主选举有亲和力。而我们的调查发现显然不支持这个假设。如何解释这种看似奇怪的数据结构呢?费孝通认为,在传统的乡土中国,既容不得“横暴权力”,也缺乏“同意权力”的根基,大行其道的是礼俗权威。维系这种礼俗权威的就是个人经验、传统习俗和社会势力(费孝通,1985)。笔者认为:无论是民间权威,还是经济能人权威,都是自发内生的,这样的权威不需要民主程序来认可。因此,有这种权威认同心理的人,更倾向于传统的权力交接方式,即上级委任制。但是,无论如何,接受并支持民主选举的人占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主张民主选举的农民,不是“大门口的陌生人(魏斐德①)”而是体制中人。表13农民的权威认同与村干部产生方式观念的交互分析选举或任命所认同的权威角色您认为村干部应该实行选举还是任命应该村民选举应该上级任命两种都行不知道频次村支书7068715651781村主任71010213454441有钱人450233192125120大姓族老42914319023821村民代表69910813163176不知道43582230253269总计645102162901808(二)支持还是不支持制度性支持是在政治认同基础上对公共权力的服从。支持还是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政治认同的结构。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效应就是能够改变原有的社会权威认同的结构,从而促使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对于缺乏强制性的村级权力来说,社会权威认同与制度性支持程度的高低,意味着权力支配或影响力的实际强弱。38①笔者借此来形容体制外或寄生于体制上的异己力量。魏斐德,1988,《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不少学者的研究认为,村民选举有助于提高村委会在村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徐勇,1997;胡荣,2001;何包钢、郎友兴,2002)。笔者的调查数据支持这个判断。表14显示了被访者对村级组织权力的认同及制度性支持的程度。表14农民的制度性支持程度支持程度主张选举或是任命农民对村委会认同与支持的程度(%)只要是民主选举的,都要支持和服从无论谁当选,都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无论谁当选,都与我无关不知道支持谁频次主张村民选举65920989431150主张上级任命40440511970185两种都行49718821997288不知道384119182314159总计582218121791782首先,看主张民主选举的被访者,有659%的人表示无论谁当选村委会,都得支持和服从村委会的自治权力。这些被访者属于阿尔蒙德和维尔巴(G.Alnaond&S.Verba)所谓的具有公民文化的人(G.阿尔蒙德等,1989)。有209%的人认为,选举出来的村委会都要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笔者交互分析显示,这一回答的党员被访者为336%,而群众被访者为188%,表明选民的政治立场同党派性有明显的关联,这也是现代政治社会的特征。其次,看倾向于任命制的被访者,选择支持村委会和支持党支部的比例一样。说明在他们心目中,村委会与党支部是一回事,都是农村基层的正式权力。而上述分析揭示出,倾向于任命制的农民,其政治认同取向主要是民间权威和经济权威(族老和老板)。在政治文化上,他们的臣民文化色彩更浓。第三看“两可派”,接近50%的被访者更加支持村委会,但他们身上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犬儒主义色彩明显,219%的被访者回答是“无论谁当选,都与我无关”。综合来看,农民的政治支持体现了权威认同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支持是认同性支持而不是被支配性的服从。(三)干群关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干群关系紧张的根源,是农民的利益遭受显性或隐性的侵害或剥夺,导致农民采取抗争性的集体维权行动或抵制性参与(郭正林,2001;于建嵘,2001)。无论如何,干群关系的实际状况是村民选举制度实施的微观社会环境。农民又是如何评价干群关系及其变化趋势的呢?表15是笔者的问卷分析结果。表15农村对干群关系变化的一般看法评价政治面貌干群关系变好还是变差了变好变差时好时差不知道频次党员58021914852324群众3912062081961395总计4262081971691719从表15可见,对干群关系及其变化持乐观态度的党员被访者比群众要高19个百分点,认为“变差”的两者都在20%左右。在总体上,超过一半的被访者对干群关系持不乐观或怀疑观望的心态。根据笔者的统计分析,政治面貌同这种评价意见的G系数为0371(0000)。不可否定,影响干群关系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改善干群关系的方式方法也就需要多管齐下。其中,村民选举是被认为是经济成本最小、社会效应最大的有效方式。那么,村民选举对干群关系的改善作用如何呢(参见表16)?表16村民选举对改善干群关系的作用分析作用政治面貌村民选举是否改善了干群关系密切了干群关系选与不选一样反而使矛盾更多说不清楚频次党员62374196107326群众4532411211851400总计4852091361701726事实上,表16与表15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两变量的G系数为056(0000)。在“党员”被访者中,认为村民选举有助于改善干群关系的是整个数据表格中的众数。在“群众”这一栏,给予积极评价的占了453%,其余的评价比较消极。在总体上,农民对干群关系的积极和消极评价平分秋色。
(四)村民选举对集体经济的影响
认为村民选举、村民自治会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历来是基层民主倡导者或促进派的理由,而村民自治的怀疑论者或反对派对这个理由嗤之以鼻(Kelliher,1997)。这样的争论还在国内继续着。那么,农民自己是如何评价村民选举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呢?表17是笔者的调查分析结果。表17村委会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分析评价主张选举还是任命村委会选举对本村经济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有促进作用有妨碍作用选与不选一样不知道频次选举569762451101169任命46714831966182两种都行37692403129164不知道13479421366164合计488862941321810表17显示,认为村民选举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促进作用的是少数,在1810个被访者(有42人没回答)中,仅有86%的人认为“没有促进作用,反而有妨碍”。无论是主张选举制还是主张任命制的,多数被访者都肯定民主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促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观点为“选与不选一个样”的人数不少,约占总数30%的人持这种意见,而且回答为“不知道”的人,其实也可以归为这一类。总之,有426%的人看不到村委会选举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分析结果是令人沮丧的。
四、简短结论
直接、公开、竞争的村民选举是一种公民赋权行动。正是有了这种公民赋权的制度安排,公民的政治权利才获得了制度化的实现途径。可以说,真正拉开当代中国宪政制度建设帷幕的不是城里人,而是在村民直选中落实政治权利的农民大众。而国家宪政制度建设的启动,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形态从人治性、工具性、阶级性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制度性、权利性和自主性的政治参与,由此彰显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效应。
通过对分布在广东26个村的1852个被访者的问卷调查分析,笔者发现762%的被访者参加过1次以上的投票选举;163%的被访者参与过1次以上的党支部选举活动;36%的被访者参加过人大代表的投票选举。尽管调查数据显示的村委会选举投票率低于政府公布的水平,但这种有选择的选举参与是真实而有意义的民主参与。统计分析表明,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开始呈现出非经济性的特征。在所有因素中,个人经济收入水平对政治参与程度的影响最微弱甚至在统计上不相关,而政治面貌及社会经历的影响最强。
人大代表选举是真正把农民同国家联系起来的制度渠道。然而,同村委会选举相比,农民在人大代表投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不高,参与率低了1倍之多。这同执政党在十六大所确立的“三个代表”的政治要求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笔者的调查也显示,农村“三个代表”的宣传贯彻活动还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这同基层党政部门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有直接的关系。从卷入式政治参与向权利性政治参与转型的完成,最终需要参与者公民意识的成熟及政治认同结构的民主化转型。我们的调查显示,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动机之中,经济利益不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权利及公共意识正处于觉醒之中。经济理性的模型不能解释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投票中的物质刺激(如误工补贴)作用在减弱,60%的被访者表示,没有物质刺激也要参与投票选举。农民对公共秩序、公共福利的关心程度在增强,这种增强对农民的选举取向有直接的影响。在所列投票选举取向的要素当中,农民认同那些办事公道、品行端正、有文化知识、敢为村民说话的候选人。狭隘的家族利益已不再是驱动农民政治参与的支配因素,起码表明被调查地区农民的家族文化观念在淡化。
正在经受民主选举洗礼的中国农民,具有一定的政治判断能力。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646%的被访者是民主选举的支持者,而且他们接受和支持体制权威。无论是对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还是对由群众推选、党员投票的党支部,都显示了他们的认同性支持。这些农民所支持的民主选举,就是要求所有村干部,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从村民代表到人大代表,都要经受村民选票的民主考验。那些不看好选举制度的被访者以及“两可派”,一是认为选举产生不了立竿见影的社会经济效果;二是在他们的权威认同结构中,族老的权威来自自发内生的传统,老板的权威来自钞票,两种权威都不能由选举来确立。我们的调查分析还表明,在中国乡村这个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民间经济、民间权威及其追随者,不一定具有现代民主制度的权威意识。因此,那种企图以西方民主的发展轨迹来圈画中国乡村民主前景的人,真有可能变成“大门口的陌生人”。
①本研究成果是笔者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研究”(02BZZ026)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主要成员是李江涛、王金洪、童晓频、郭巍青、徐勇、胡荣、肖唐镖、王春生、邹静琴、王杰珍、刘鹏。问卷调查由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联合进行,调查员主要来自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1999级大学生,所有问卷均由调查员访问与记录。
参考文献:程同顺,2000,《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郭正林,2001,《当代中国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卷,春夏季。G.阿尔蒙德、S.维尔巴,1989,《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何包纲、朗友兴,2002,《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贺雪峰,2000,《村委会诸环节的调查与分析———湖南省四十个县村委会选举信息回访活动报告》,乡镇论坛杂志社、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农村处《1999年度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胡荣,2001,《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李连江,1997,《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吴国光《九七效应:香港、中国与太平洋》,太平洋世纪研究所出版。刘喜堂,2001,《湖南省1999年度40个县村委会选举数据分析报告》,张明亮主编《村民自治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出版社。欧博文,2001,《村民、选举及公民权》,香港“第二届中国大陆村级组织建设学术讨论会”。孙龙、仝志辉,2002,《程序引导与村委会选举的规范化———吉林省5县40个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调查分析与思考》,刘亚伟编《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西北大学出版社。吴淼,2002,《村委会选举质量的量化分析———以福建省九市2000年度村委会换届选举统计数据为依据》,《无声的革命———村民直选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肖唐镖、邱新有、唐晓腾,2001,《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谢子平,2001,《福建省2000年村委会选举调查数据分析报告》,《村民自治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出版社。徐勇,1997,《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利益与体制:民主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徐勇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于建嵘,2001,《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周晓虹,2000,《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后时代的比较》,《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7卷,秋季。
- 上一篇:政府经济学范文
- 下一篇:政府经济管理规范化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