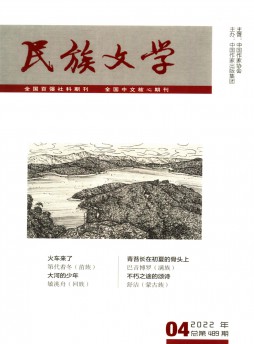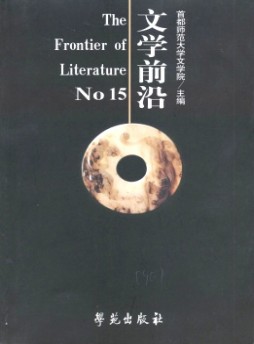文学批判功能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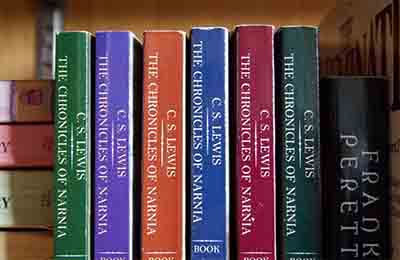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当前作家、艺术家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今天这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时期,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其主要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是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行为进行审视与反思。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立场或理论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因为现代文化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在坚持“边缘”、与“中心”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对处于“中心”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单维化趋势所进行的批判。任何一种思想潮流或文化观念一旦获得中心地位,就有可能变为一种强势话语,从而产生排他性,成为排斥边缘话语的霸权话语,导致人类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失衡。一个时代的健康的精神环境应当是一种各种文化思想、价值取向相互制衡、良性互补的环境,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艺术家的使命,就是以自己的特殊劳动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和主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于它,相反要审视、反思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负面的社会效果,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批判的声音,从而在与主流话语保持张力中,产生相互制衡机制,促进时代文化的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样,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永远是边缘的立场,至于这个立场的具体内容、批判的具体对象则可以甚至必然根据批判者或批判话语所处的“语境”而定,并且随着这个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落实到当前的社会现实,我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占据主流的是“发展就是一切”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发展”(或“进步”、“历史进步”)又普遍地被理解为经济、物质或科技的发展,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历史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一直是缺席的,或者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这种情况在其他一些第三世界的后发展国家同样是十分普遍的,在那里,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历史发展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就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
中西方的现代文学艺术史都充分证明:作家艺术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是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中的科技专家、经济学家等,常常更多地把历史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文关怀在他们那里处于“边缘”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艺术家的“边缘”立场就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除了上述说的精神文化环境的平衡以外,还在于:由于评价角度的不同,作家艺术家更多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特别是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人类的历史上,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精神道德的完善并不同步甚至相互对立,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种悖论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维度与人性完善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界,从韦伯、马克思、海德格尔,到霍克海墨、阿多诺、马尔库塞、福柯、哈贝马斯,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看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之间的不一致[科层官僚化的弊端(韦伯)、工具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对价值理性与信仰的挤压(霍克海墨)、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中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攫取型的原子式孤独个体(弗罗姆、克尔凯郭尔)、现代科学知识与社会控制以及极权主义统治的关系(福柯、霍克海墨)],科技的发展的双刃剑的性质。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分离(海德格尔),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坚决站在非主流立场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几乎都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物质主义、工具理性、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度等),现代派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持批判或否定的立场。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意识形态(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导的思想意识)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些与社会发展的主流相左的作家和作品,并不妨碍反而增强了其思想与艺术价值。常言道: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一个在文学创作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作家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包括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时候常常有两个尺度,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种尺度的不同组合关系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作追求与作品类型。其中有两个基本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吻合模式或统一模式,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要么是颂歌式的作品,要么是诅咒式的作品。在颂歌式的作品中,被作家从历史角度赋予肯定性(或否定性)的人物或事件,同时也是从作家从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或事件。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创作模式一直占主流。《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以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这样的作品。作品中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高大泉),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一定同时是罪该万死的恶棍(如王世仁、南霸天)。由于这类作品在人文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上没有出现分裂或悖反,因而在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具有单纯、明朗的特点。这一模式也产生过一些艺术精品,这是不应否定的。但是毋庸讳言,这种单纯与明朗常常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性的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的。它人为地掩盖或至少是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悲剧性二律背反(即历史与道德的悖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反、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悖反)现象,慷慨地赋予历史发展以人文道德与价值上的合法性,客观上起着美化现实、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同时,这种创作模式也忽视、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人的道德品质与他(她)的历史命运之间的悲剧性悖反(好人、君子没有历史前途,而坏人、小人倒常常成为历史的弄潮儿。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悲事实)。由于看不到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所以在这种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一种简单化的历史与道德的人为统一。仿佛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道德的进步以及人性的完善,我们的选择总是十分简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就是道德上的完善过程,好人必然而且已经有好报,坏人必然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里反映出某些作家常以时下的口号为规范,而不是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为创作之资源。
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人文道德尺度的错位模式或二元对立模式,它所产生的是挽歌式的作品: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人物或事件恰恰是缺乏道德合理性的,而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事件和人物则失去了历史的必然性,处于被历史淘汰的地位。这种作家与作品看到了并且勇敢地正视历史与道德地悲剧性地二律背反,看到了历史的所谓进步付出的常常是良知、正义和诗意感情的代价,正因为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与作家艺术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是充满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与悲悯,他们常常既不是简单、天真地让历史发展服从自己的道德目标,也不是(或者说更不是)简单地认同历史的所谓“发展规律”,化身为历史的人、代言人。他们知道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文人的“悲鸣”从来抵挡不住历史前进的铁蹄,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凝重的悲剧感和和悲闵的情怀。但是他们决不简单认同历史的“铁律”,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记录了历史的悲剧性的悖反,他们的社会历史见解有时是反潮流的甚至是反历史的,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有些错位乃至相悖,有时甚至还是十分“幼稚”的。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此类对历史发展唱“反调”、唱挽歌的作家作品,挽歌是专门唱给已经或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美者与善者的(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它们没有历史前途,但具有道德的正当性与审美价值,从而让作家梦魂萦绕,悲从中来。既有历史前途又有道德正当性的东西只能产生颂歌,没有历史前途又缺乏道德正当性东西则产生咒语。它们都产生不了挽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命运,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则是惟利是图的恶棍。
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中,也不乏这种挽歌式的作品。比如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和《沙灶遗风》,王润兹的《鲁班的子孙》等就是属于第二种模式的作品,它属于在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两者之间“徘徊”并保持张力的作品。《最后一个渔佬儿》写到一个老年的渔夫坚持用原始的非现代的工具和方式打鱼,他跟不上也不想跟上时代历史的发展,他迷恋原来的打鱼方式工具,迷恋与这种工具这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在一个现代化的捕鱼工具与捕鱼方式的挤压下,在人们都追赶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下,这个最后的渔佬儿显得既过时,但他的顽强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精神又显得非常可贵。《鲁班的子孙》写一对木匠父子,老木匠为人正直,不惟利是图,但是又顽固坚持原始的制作家具的方式,在时代的大潮面前显得很落伍了;而他的儿子小木匠则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弄潮儿,他及时地改用了现代化的工具和家具制作方式,结果生意比老爸好得多,但是他也沾染了市场社会的斤斤计较、惟利是图的习气,在道德上作者明显地否定这个形象。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历史进步与道德关怀的错位和“对峙”状态,作家既不放弃历史理性的维度,写出了历史的客观趋势,但也决不为了迁就历史而放弃道德和人文的维度。这使得作品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事物或人物并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而反过来,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事物或人物却常常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这样就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写出来了。前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金发表过一部题为《告别马焦拉》也是这样的。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一个小岛。春天来了,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生:这里要修建水电站,水位要提高几十米,全岛都将被淹没。年轻人站在历史理性一边,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新的生活,离开这个小岛出去见世面,去过更富有的日子,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作家肯定了他们的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但是老年人却站在怀旧,他们要维持自己对于这一片土地的感情,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岛上的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温暖的,不可或缺的;这里有他们绿色的森林,有他们宁静的家园,有他们的初恋之地,有他们眷恋着的一切。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你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而是你们为机器劳动,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你们图什么呢?作者同情、理解这些怀旧的人,认为他们(她们)的怀旧情绪是美好的,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作者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中徘徊,在“新”与“旧”中徘徊。新生活必然要取代旧生活,然而旧生活就没有价值吗?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告诉我们: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现代化的生活不是所有人都向往的,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历史的复杂性常常体现在: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并不都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而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也不都是没有合理性能够的。现代化被我们带来的绝对不是完美的天堂。
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回到人类历史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的问题。历史之所以呈现悲剧性的二律背反,是因为两个同样是正面的价值、同样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如物质发展与道德完善、现代化城市化与美丽宁静的田园风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常常却不能共存,必得牺牲一放才能发展另一方,它们之间呈现出悲剧的对抗。这也就是黑格尔说的“悲剧”的含义。
- 上一篇:生态人理论蕴涵与价值范文
- 下一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范文
精品推荐
- 1文学与文化论文
- 2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 3文学专业论文
- 4文学价值论文
- 5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 6文学作品分析论文
- 7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利与弊
- 8文学作品论文
- 9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 10文学写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