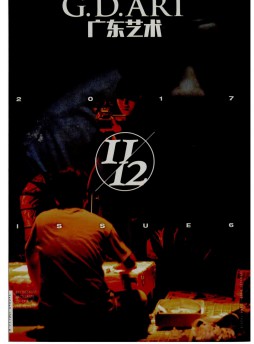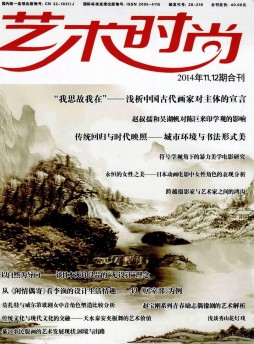艺术哲学的新方向分析范文
时间:2022-03-07 04:47:44

一
主客二分即主—客关系式,由柏拉图开其先河,其明确的建立和发展则相伴于笛卡尔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到黑格尔达到其完善的顶峰。这种思维模式要求作为主体的人把本来外在于主体的客体作为对象来加以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最终认识到特殊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即本质、概念,从而能说出某事物是“什么”。这“什么”就是各种特殊事物的本质、概念。例如,当认识到或者能说出某物是“桌子”时,这里的“桌子”就是各种特殊的桌子的普遍性,是它们的本质、概念。可以说,“什么”乃是主—客式所要达到的目标,主—客式由此而崇尚理性、概念,故这种哲学又可叫做概念哲学。西方传统艺术哲学基本上以所谓典型说为其核心,典型说就是以概念哲学为其理论基础的:典型就是作为普遍性的本质概念,艺术品或诗就在于从特殊的感性事物中见出普遍性、见出本质概念。柏拉图认为感性事物是概念(“理念”)的影子,而艺术品或诗不过是对感性事物的摹仿,因而是影子的影子,故他要拒斥诗人、画家于他的国门之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学家描述已发生的事情,诗人则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诗所言说的大多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东西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普遍性就是典型,诗就是要写出典型。亚里士多德还把典型与理想联系起来,认为艺术品应当按事物“应然”的理想去摹仿,例如画美人就要画出集中美人之优点的理想的美人。这种典型显然是以本质概念为依归,实源于柏拉图的“理念”。
“理念”本来就有普遍性、理想性的意思,艺术品应以“理念”为原型来加以摹仿。西方近代流行的“典型”一词与柏拉图的“理念”有密切关系。康德虽然承认审美意象所包含的意蕴远非明确的普遍性概念所能充分表达,这比亚里士多德把诗人所描述的可能性限制在同类的普遍性范围之内的思想要前进了一步,但康德没有充分发挥这一思想观点,而且他的哲学中的“规范意象”,显然未脱旧的追求普遍性概念的窠臼。近代艺术哲学的典型观已经把重点转到特殊性,重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但即使是强调从特殊出发的歌德,也主张在特殊中显出普遍,所谓“完满的显现”就是要显现出本质概念,这种艺术观仍然是走的概念哲学的旧路。西方艺术哲学中有所谓艺术摹仿自然的主张,不用说,是以自然为原型,以艺术品为影像的主—客式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批评摹仿说,认为摹仿说意在复制原物,而实际上摹仿总是“落后于原物”,但黑格尔所谓“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仍然是要求艺术品以追求理念即普遍性的本质概念为最高目标,凡符合艺术品之理念的就是真的艺术品,尽管他也要求典型人物应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我国文艺理论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所广为宣讲的典型说,认为只有能显现一件事物之本质或普遍性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此种艺术观完全是西方传统典型说之旧调重弹,其理论基础是西方旧的概念哲学,它的要害就是把审美意识看成是认识(即认识事物的本质概念,认识事物是“什么”),把美学看作是主—客关系式的认识论。在三十多年前的那场美学争论中,有的参与者曾明确宣称,美学的哲学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这就充分点出了他们所崇奉的旧的艺术哲学的核心。
二
黑格尔逝世以后的一些西方现当代哲学家如狄尔泰、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都不满意传统的主—客式的概念哲学,而努力寻求一种超越主—客式、超越概念哲学的道路。这是西方哲学的一次新的重大转向。狄尔泰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不止是主体与客体的外在关系,人生的意义不止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搭上一座认识的桥梁(所谓“主客统一”)而已,人生乃是作为知(认识)情意(包括本能、下意识等等)的人与世界万物融合为一的整体。尼采主张摒弃主体、客体的概念。他斥责柏拉图抬高世界、贬低感性世界,是因为“柏拉图在现实面前是懦夫”。尼采明确断言,艺术家“热爱尘世”,而旧形而上学把人引向概念世界,使人生变得“枯竭、贫乏、苍白”。他提倡“学习善于忘却,善于无知,就像艺术家那样”③。
这也就是提倡超越主客、超越知识以达到他的“酒神状态”———一种与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尼采还认为世界万物不过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实体或本质概念。海德格尔则明确地要求返回到比主—客关系更本源的境域,或者说是一种先于主客区分的本源。此境域由普遍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用尼采的话来说)“构成”,每个人都是这种联系、作用、影响的聚焦点,有的联系、作用、影响是直接的、距离较近的、有形的、重要的,有的是间接的、距离较远的、无形的、不重要的。借用佛家所讲的“因缘”来说,一事一物皆因缘和合而生,有直接与以强力者为因,有间接助以弱力者为缘,事物皆与其境域相互构成。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像灵魂与肉体的关系一样:无世界,则人成了无躯体的幽灵;无人则此世界成了无灵魂的僵尸,是无意义的。我为了通俗起见,经常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把这种关系称为“天人合一”(当然这里要撇开二者的不同之处)。“天人合一”就是万物一体:万物各不相同而又互相融合,一气相通,这里没有任何二元之分,包括主客之分、物我之分。这万物一体的境域是一切事物之所以可能的本源或根源,它先于此境域中的个别存在者,任何个别存在者因此境域而成为它之所是。人首先是生活于此万物一体的“一体”之中,或者说天人合一的境域之中,它是人生的最终家园,无此境域则无真实的人生。但人自从有了区分主客的自我意识之后,就忙于主体对客体的追逐(无穷尽的认识与无穷尽的征服和占有)而忘记了对这种境域的领会,忘记了自己实际上总是生存在此境域之中,也就是说,忘记了自己的家园。
诗意或者说审美意识,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打开这个境域,就是一种返回家园之感,也可以说,就是回复或领会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自脱离母胎以后,先总是有一个短期的不分主客的无自我意识的阶段,然后才区分主客,产生自我意识,至于领会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从而超越主客二分,则是有了审美意识的人或少数诗人之事。黑格尔青年时期曾经把艺术、审美意识置于哲学、理性概念之上,到了他的哲学成熟期则反过来把哲学、理性概念置于艺术、审美意识之上。他在阐述其成熟期的这套理论时曾明确地把主客“二分”的态度看成是“对于对象性世界的散文式的看法”而与“诗和艺术的立场”“相对立”④。从黑格尔这里也可以看到我国三十多年前关于美是主客二分关系的观点之陈旧。只是黑格尔仅仅认为从无自我意识到有自我意识的“中间状态”(或者说是一种“初醒状态”)才有诗兴和艺术的起源,他不知道有通过修养和陶冶而达到的超越主客的诗意和艺术,就像老子所说的超知识的高级“愚人”状态或“复归于婴儿”的状态即真正的诗人境界。黑格尔贬低艺术,他是主客式的散文哲学家,而非诗人哲学家。实际上在他以前的主—客式的旧形而上学也都认为个人的意识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都只不过是从原始的主客不分到主客关系而已,他们只知道在主客关系框架内通过认识而达到的主客统一,而基本上不承认有超越主客关系的诗意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所以在他们看来,真实的世界只能是“散文式的”,人们最终能达到的只是一些表达客体之本质的抽象概念。哲学成了远离诗意的枯燥乏味、苍白无力、脱离现实的代名词。海德格尔一反黑格尔集大成的主—客式的主体性哲学,强调对“人与存在的契合(Entsprechen)”⑤的领悟或感悟,认为人一旦有了这种感悟,就是聆听到了“存在”的声音或呼唤,因而感到一切都是新奇的、“令人惊异的”,都不同于按平常态度所看待的事物,而这所谓新奇的事物,实乃事物之本然。所以海德格尔说:“哲学就是与存在者的存在相契合”⑥;又说:“诗人就是听到事物之本然的人”⑦。海德格尔显然把哲学和诗给合成了一个整体。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认为,因感悟到“人与存在的契合”而引起的新奇或惊异,并不是在平常的事物之外看到另外一个与之不同的事物。他认为“在惊异中,最平常的事物本身变成最不平常的。”⑧所谓最平常的,就是指平常以主客式态度把事物都看成是与主体对立的单个存在者(being)。海德格尔认为以此种态度看待事物,存在不可能敞开,而在“人与存在契合”的“惊异”中,同样的平常事物被带进了“存在者的整体”(dasSeiendeimGanzen),事物不再像平常所看待的那样成为被意识人为地分割开来的东西,而显示了“不平常性”,从而“敞开”了事物之本然———敞开了事物本来之所是。所以要达到诗意的“惊异”之感,只有超越主客关系,进入一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人与存在相契合”的境界之中。
海德格尔对于“人与存在相契合”的感悟所引起的诗意的新奇、“惊异”之感的看法,和文学家柯勒律治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柯勒律治没有那么多的哲理分析。柯勒律治说:“渥兹渥斯先生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通过唤起人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他去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可是由于太熟悉和自私的牵挂的翳蔽,我们视若无睹,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对它既不感觉,也不理解。”⑨文学家柯勒律治的这段话如果用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哲学语言来概括,那就可以这样说:世界本是一个“人与存在相契合”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事物的意蕴是无穷的,只因人习惯性地以主客关系的态度看待事物,总爱把事物看成是主体私欲的对象,人对这样观察下的事物熟悉到了麻木的程度,以致受其遮蔽,看不到这平常事物中的不平常的魅力,看不到其中的美丽和惊人之处。海德格尔一反西方旧形而上学,把哲学和诗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关于在“人与存在相契合”的感悟中所发现的平常事物本身中的不平常性的观点和论述,与诗人、文学家不谋而合。任何一个哲学家,即使是主张以主客关系为最高原则的哲学家,其本人实际上也都有自己的“与存在相契合”的境界。如果我们的哲学家们能沿着当今的哲学和艺术哲学的新方向像诗人创作诗的作品一样,创作出表现个人独特境界的新颖的、“令人有惊异之感”的哲学作品,那该是一幅多么美妙而令人惊异的景象啊!人类的生命和生活本来是美妙而令人惊异的。
三
在人所融身于其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境域中,每个事物都是一个聚焦点。就一事物之当前显现的方面来说,它是“在场的东西”,就与一事物相关联的背后隐蔽的方面来说,乃是“不在场的东西”。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互构成一个境域。说此境域是万物之本源,意思也就是说,不在场的、隐蔽的东西是显现于在场的东西的本源。按照这种新的哲学方向和观点来追究一事、一物之本源,则需要从在场者追溯到不在场者,而不是像旧的概念哲学那样到抽象的概念中去找本源,这里的不在场者不是概念,而是与在场者一样具体而现实的东西。哲学由旧方向到新方向的转变就这样把人从抽象的概念王国转向具体的现实王国,由天上转向人间,由枯燥、贫乏、苍白的世界转向活生生的有诗意的生活世界。。人本来就是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这样,哲学本身就是艺术哲学。通常把艺术哲学(或者用我们通常所用的术语来说,美学)看成是哲学的一个分支的看法应该说是过时了。按照这种新的方向和观点,文艺作品不再是以写出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为主要任务,而是要求通过在场的东西显现出不在场的东西,从显中看出隐。只有在显隐相互构成、人与世界相互构成的整个联系、作用、影响之网络中,在此本源中,才能看到一事物的真实性。诗不简单是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引发或者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反”到作为本源意义的境域,是看到真理。所以海德格尔说,有诗意的艺术品乃是“真理的场所”。真与美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里要着重说的是这种寻本求源的新方向与旧形而上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前面说到旧形而上学家的概念哲学要求说出事物是“什么”,与此相对的是,新的哲学方向则要求显示事物是“怎样”(“如何”)的。意思就是要显示事物是怎样从隐蔽中构成显现于当前的这个样子的。
“什么”乃是把同类事物中的不同性———差异性、特殊性抽象掉而获得的一种普遍性,“怎样”则是把在场的东西和与之不同的、包括不同类的不在场的东西综合为一,它不是在在场与不在场之间找共同性。这里的“怎样”不是指自然科学如生物学、化学等所研究的动植物怎样生长、化合物怎样化合的过程,而是从哲学存在论的意义上显示出当前在场事物之背后的各种关联,这些背后的“怎样”关联,并不像自然科学所要求的那样需要出场和证实。例如:从梵•高画的农鞋显示出隐蔽在它背后的各种场景和画面即各种关联:如农夫艰辛的步履,对面包的渴望,在死亡面前的颤栗,等等。正是这些在画面上并未出场的东西构成在场的画中的农鞋。总之,“怎样”说的是联系,是关系(显隐间的联系或关系),或者用佛家的话说,是“因缘”,而不是现成的东西———“什么”。这些关联的具体内容就是“何所去”、“何所为”、“何所及”之类的表述关系,表述相互纠缠、相互构成的语词。我们平常只是笼统地讲事物的普遍联系,而不讲联系中的显现方面与隐蔽方面,不讲联系所包含的各种具体内容,因而不能具体显示当前在场的事物是“怎样”联系而成———“怎样”因缘和合而成,也不能具体显示人生的诗意。
例如一个酒壶,如果按照传统形而上学,酒壶由泥土做成,是壶形,可以盛酒,如此,就说明了酒壶是“什么”。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酒壶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可以用来敬神或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或者还可以借酒浇愁,……等等。这样,就从显隐之间的各种关联的角度显示了酒壶是“怎样”构成的,酒壶的意义也就深厚得多。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把美学看成是认识论,把审美意识归结为把握“什么”的认识活动,这种旧的艺术哲学观点该多么贫乏无味,多么不切实际。“怎样”的观点,说明显现与隐蔽的同时发生和不可分离性。对一件艺术品的欣赏,乃是把艺术品中显现于当场的东西放进“怎样”与之相关联的隐蔽中去,从而得到“去蔽”或“敞亮”的境界。倒过来说,“去蔽”或“敞亮”就是把隐蔽的东西带到当场或眼前。离开了“怎样”与之相关联的隐蔽,根本谈不上在场的“敞亮”。也可以说,是“怎样”打开了“敞亮”。所以海德格尔一再申言,宁要保持着黑暗的光明,不要单纯的一片光明,一千个太阳是缺乏诗意的,只有深深地潜入黑暗中的诗人才能真正理解光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艺术哲学之弊就在割裂“敞亮”与“隐蔽”,把“敞亮”绝对化、抽象化而奉单纯在场的永恒性(本质概念就是永恒的、单纯在场的东西)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海德格尔所代表的新的艺术哲学方向就是要强调隐蔽对敞亮、不在场对在场的极端重要性。美的定义于是由普遍概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转向为不出场的事物在出场的事物中的显现。
四
把显现与隐蔽综合为一的途径是想象。旧形而上学和艺术哲学所借以达到本质概念的途径是思维,即把特殊的东西一步一步地加以抽象从而把握普遍性。想象在旧形而上学看来,不过是单纯在场的原本的影像,应该加以贬低或排斥。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几乎是第一个打破这种关于想象的旧观点的哲学家。他说:“想象是在直观中表象出一个本身并不出场的对象的能力”⑩。康德的这一定义虽然仍有从影像追溯到原本的旧观点的痕迹,但他已经把想象放在一个既有在场又有不在场的领域。经过胡塞尔的发展,想象则更明确地成了把不在场的东西与在场的东西综合为一的一种能力。其实,任何一个简单的“东西”(thing),也要靠想象才能成为一个“东西”。一颗骰子,如果单凭知觉,则知觉到的只能是一个无任何厚度的平面,因而也就不成为一个“东西”,我们之所以能在知觉到一个平面的同时就认为它是一颗立体的骰子,是一个有厚度的“东西”,乃是因为我们把未出场的其他面或者说厚度通过想象与在知觉中出场的方面综合为一个整体的结果。所以想象乃是超越在场者,把事物背后隐蔽的方面综合到自己的视域之内,但又仍然保留其隐蔽性,而非直接让它在知觉中出场。想象不像旧哲学那样只注重划定同类事物的界限,而是注重不同一性,不仅注重同类事物所包含的不同的可能性,而且注重超越思维已概括出来的普遍性界限之外,达到尚未概括到的可能性,甚至达到实际世界中认为不可能的可能性。
思维总是企图界定某类事物,划定某类事物的界限,但这种界限在无穷尽的现实中是不能划定的。我们应该承认思维的局限性,但也正是在思维逻辑走到尽头之际,想象却为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域。例如“天下乌鸦一般黑”,但下一次观察到的乌鸦可能不是黑的,这就是我们运用想象的结果,它是一种想象的可能性———一种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但尚未实际存在过的可能性并非不可能,想象的优点也正在于承认过去以为实际上不可能的东西也是可能的。想象扩大和拓展了思维所把握的可能性的范围,达到思维所达不到的可能。思维的极限正是想象的起点。想象并不违反逻辑。例如说下次观察到的乌鸦可能不是黑的,这并不违反逻辑,但它并非逻辑思维之事。可以说,想象是超逻辑的———超理性、超思维的。逻辑思维以及科学规律可以为想象提供一个起点和基础,让人们由此而想象未来,超越在场的东西,包括超越“恒常在场的东西”。科学发现和发明主要靠思维(包括感性直观),但也需要想象。科学家如果死抓住一些实际世界已经存在过的可能性不放,则眼光狭隘,囿于实际存在过的范围,而不可能在科学研究中有大的创造性的突破。在科学的进展过程中时常有过去以为是颠扑不破的普遍性原理被超越,不能不说与科学家的想象力,包括幻想,有很大的关系。西方现当代许多哲学家认为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敞开一个使事物如其本然的那样显示出来的整体境域,没有想象,就没有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现实整体,诗意和艺术的魅力也不可能产生。
五
隐蔽的东西的无穷尽性给我们带来了对艺术品的无穷想象———无穷玩味的空间。过去我国有的文艺理论家认为,只要从个别事物中写出和看出普遍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哲学上的根据。其实,如前所述,一种普遍性概念所界定的事物范围无论如何宽广,总是有限度的,我们从这种艺术作品中所能想象—玩味的,充其量只能是与此个别事物同属一类的其他事物,因此这种艺术品所给人留下的可供想象—玩味的可能性的余地显然也是有限度的,而不是无穷的。新的艺术哲学方向要求从显现的东西中所想象—玩味的,不仅冲破某一个别事物的界限而想象—玩味到同类事物中其他的个别事物,而且冲破同类的界限,以想象—玩味到根本不同类的事物。两相比较,真正能使我们想象—玩味无穷的艺术品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莫里哀的《伪君子》倒是写出了典型人物或者说同类人物的普遍性特点,而不是某一个别人的精确画面,但它给人留下的想象—玩味的空间并不是无穷的。
犹有进者,旧的典型说在崇奉普遍性概念的哲学指引下,总是强调把现实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作集中的描写,写英雄就把现实中各种英雄的性格集中于英雄一身,写美人就把现实各种美人的美集中于美人一身,于是艺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都被普遍化、抽象化了,虽然也能在一定限度内给人以想象和启发,但总令人有某种脱离现实之感。新的艺术哲学方向所要求显示的在场者背后的不在场者,与在场者一样,仍然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这样的艺术作品所描写的人和事和物也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现实,而非经过抽象化、普遍化的东西。当然,它也不能是具体现实物的照搬,否则,就不能给人以想象和玩味了。中国古典诗在从显现中写出隐蔽方面,在运用无穷的想象力方面,以及在有关这类古典诗的理论方面,实可与海德格尔所代表的艺术哲学互相辉映,或者用人们当前所习用的话来说,两者间可以实行中西对话、古今对话。刘勰《隐秀篇》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他所讲的隐和秀,其实就是讲的隐蔽与显现的关系。
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显隐说未尝不可以译为隐秀说而不失原意。文学艺术必具诗意,诗意的妙处就在于从“目前”的(在场的)东西中想象到“词外”的(不在场的)东西,令人感到“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这也就是中国古典诗重含蓄的意思。但这词外之情、言外之意不是抽象的本质概念,而仍然是现实的,只不过这现实的东西隐蔽在词外、言外而未出场而已。抽象的本质概念是思维的产物,词外之情、言外之意则是想象的产物,这也就是以诗的国度著称的中国传统之所以重想象的原因。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所描写的画面真是状溢目前,历历可见,可谓“秀”矣。但如果仅仅看到这首诗的画面,显然还不能说领会到了它的诗意。实际上这首诗的妙处就在于它显现了可见的画面背后的一系列不畏雨横风狂而泰然自若的孤高情景,这些情景都在诗人的言外和词外,虽未出场,却很现实,而非同类事物的抽象普遍性,虽未能见,却经由画面而显现。当然这首诗的“孤舟”、“独钓”之类的言词已显露了孤高之意,有不够含蓄之嫌,但这只是次要的,其深层的内涵仍然可以说隐蔽在言外词外而有待人们想象。诗人之富于想象,让鉴赏者从显现的东西中想象到隐蔽的东西,还表现在诗人能超出实际存在过的存在,扩大可能性的范围,从而更深广地洞察到事物的真实性。我们通常把这叫作夸张。李白《秋浦歌》之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这里的极度夸张,其实就是想象的一种极端形式“幻想”,按胡塞尔的说法是一种对实际存在中从未出场的东西的想象。白发竟有三千丈之长,此乃实际世界中从未有过的,诗人却凭幻想,超出了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之外,但这一超出不但不是虚妄,反而让隐蔽在白发三千丈背后的愁绪之长显现得更真实。当然,诗人在言词中已经点出了愁字,未免欠含蓄,但这当另作评论。一个毫无想象力的人也许会凭感觉直观和思维作出白发一尺长或两尺二寸长这类的符合实际的科学概括,但这又有什么诗意呢?如果说科学家通过幻想,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发现和创造性的发明,那么诗人则是通过幻想以达到艺术的真实性;如果说科学需要幻想是为了预测未来(未来的未出场的东西),因而期待证实,期待未出场的东西的回答,那么诗意的幻想则不期待证实,不期待未出场的东西的回答,它对此漠不关心,而只是把未出场者与出场者综合为一个整体,从中显示出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司马光《续诗话》对这两句诗作了深刻的剖析:“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从司马光的剖析中可以看到:“山河在”和“草木深”都是“状溢目前”的在场者(“秀”),但它们却显现了不在场(“隐”)的“词外之情”———“无余物”和“无人”的荒惊情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显现是想象的显现,想象中的东西仍保留其隐蔽性,只有这样,这两句诗才有可供玩味的空间。若让想象中的东西在言词内出场,把杜甫的这两句诗改成为国破无余物,城春无人迹,那就成了索然无余味的打油诗了。杜甫的这两句诗是中国古典诗中重言外意的典型之一,司马光的赏析则深得隐秀说之三昧,可与海德格尔显隐说的艺术哲学相呼应。像杜甫这样的由在场想象到不在场的中国古典诗,显然不是西方旧的典型说所能容纳的,其所给人留下的想象空间也不是按典型说所写的艺术作品所能比拟的。总括以上所说,我以为从主客关系到超主客关系,从典型说到显隐说,从重思维到重想象,从重普遍本质到重具体现实,乃是当今艺术哲学的新方向。把中国的隐秀说和中国古典诗词同西方现当代艺术哲学联系起来看,则虽古旧亦有新意,值得我们特别加以重视并作出新的诠释。
- 上一篇:拆除镇村区域违法建筑工作计划范文
- 下一篇:艺术类英语的教学探究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