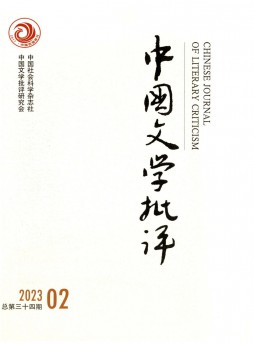文学批评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建构范文
时间:2022-06-19 03:24: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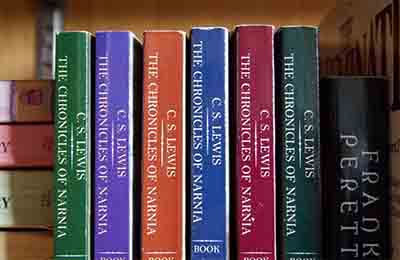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一、批评意识的契合与民族认同的自觉
在西部文学的大视野中,宁夏“三棵树”的写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他们总体性的定位或许更能说明一切,如有评论者这样评价陈继明的小说,“其乡土小说对转型期西部农村经济秩序和乡村传统道德文明体系的崩溃、乡村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乡民在金钱诱惑下的人格扭曲和人性异化都有精细的表现……其独特之处就在于穿透喧哗都市的表层生存风景,发现和揭示转型时期都市人的浮躁和抑郁心态所导致的非理性行为,直逼人物内心微妙、复杂的情绪变化与心理冲突,亦即‘陈继明式的情绪骚动’,并将之引向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揭蔽与追寻,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心理分析和存在的哲理色彩”。以修史见长的评论家,其判断往往高屋建瓴,但高度的概括往往流于以偏概全的评论姿态,如果单纯从陈继明创作的表象来看,对陈继明这样的评价也无可厚非,作为域外论者受题材论的影响,致使结论多少带有先入为主的嫌疑,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进一步体验与思考了陈继明已经体验与思考过的观念,但是却不够深入。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陈继明文学价值的定位如果放置在现代主义背景下,这样的结论则被极度类型化,也就遮蔽了小说家的独特性。而作为域内论者的牛学智洞悉了文学史家的偏颇之处,通过与陈继明本人的对话,触及作家本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及创作思维,也揭示出陈继明创作之中易被掩饰的部分,“细读陈继明的某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品,感觉他并不是自闭式的心理分析,他对人物精神存在性的剖析是严重地介入现实结构,并且眼光向外的。或者说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物的现实处境、历史处境”。结合这句论断,再回到陈继明的小说《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这篇小说“以深刻的洞察力敏锐而准确地捕捉到了当下纷扰社会情势下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心理———‘烦着呢’,并揭示出了这种异常的社会心理所蕴藏的巨大危险性”。陈继明对小说人物的刻画,虽侧重于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创作风格———“陈继明式的情绪骚动”,但陈继明创作的旨归是指向社会现实,他的心理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介入现实结构中来。牛学智的观点显然要比域外评论家的定位更到位,尤其是牛学智在论及陈的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时,指出小说之中的“父性”问题所触及的文化反思,得到了陈继明的认可。究其原因,在于论者与作家本人在对社会的认知上都不约而同地归结到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反思这一层面。这要比有些论者动不动就在“人性”“道德伦理”等常规的小视域中打转转要高明了许多。批评意识的契合还源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同一民族情结所具有的认知趋同的自觉。这一点在对石舒清的评论中得到较为明显的应验。文学史家对石舒清的评价,将石舒清放置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下来谈及,身为回族作家的石舒清,其文学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在他的小说中,常常伴有一些回族宗教礼仪、婚丧嫁娶、生活习惯等生活场景,表现出回族文化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特殊的心理内蕴。他对自己的民族身份充满着强烈的认同。“我更庆幸我是一个回族作者。……回族民族,这个强劲而又内向的民族有着许多不曾表达难以表达的内心声音。这就使得我的小说有无尽的资源。”
伴随着石舒清文学创作的不断获奖,石舒清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对石舒清的评论,如果从民族认同这一角度,回族评论者对石舒清的评论或许更为恰当,因为他们与作家本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传统,石舒清小说之中反映出来的民族意味、民族表达尤其是作品灵魂的民族精神的张扬,都会在无意识之中触动回族评论者的神经。因此,从他们的评论文章中,感受回族这一共同体特有的民族文化魅力,尤其是涉及宗教、民俗等独有的民族符号时,回族评论者的解读无疑更为准确到位。考量他们的评论,不仅是一种批评意识的契合,更是一种民族认同的自觉。这一点,域外学者已经意识到评论的失语,在对石舒清名篇《清水里的刀子》分析中,文学史家认为:“马子善老人从牛的举止中得到启迪,心情趋于宁静。这种在汉族人、现代都市人中罕见的内心令都市读者怦然心动。事实上,石舒清的用心和期望也正在这里”。这样的解读对于熟识回族文化背景的回族论者而言是不能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判断显然是不熟悉回族文化背景的可笑误读。同一细节,回族论者杨文笔写道:“小说表面是在讲述一头即将献祭的牛为‘有一个清洁的内里’作为通向彼岸世界的门票而不食不喝的神奇故事,其深层内涵体现着回族人生活中讲究清洁和心灵洁净以追求‘清真人’的精神理念。如此马老汉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死期,这不仅仅是‘他会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一件洁洁爽爽的衣裳’,更是他要为自己收拾和准备一个清洁的内里,清清洁洁地归真复命”[9]。杨文笔从回族群体的民族理念与精神追求去解读作品,这首先是一种民族认同的自觉,换句话说,石舒清的“用心和期望”应该是民族习性的使然,对比之中,杨文笔的结论更符合石舒清意识深处的生命体验。
二、终极关怀与精神价值的建构
谈及西部文学,在人们常规的阅读思维中,总觉得西部文学与现代化是不能对等的,与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与“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相比,对西部的评价,更确定说是一种文化想象,总是与原始、荒凉、野性这样的描述相联,这可能源于西部特有的地理风貌,可实际上,“‘真正的西部’有大漠、戈壁和荒原,也有自己的现代城市”。但从文学这一视角看去,西部文学反映现代城市有影响的小说是比较匮乏的,西部文学还是以乡土文学见长。不言而喻,西部的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接受并没有化成血肉,变成生活习惯,大量的西部作家从人生经历来看,多有着农村的生活背景。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首先是在人生经历与个人记忆中寻找创作的题材。这一点,在宁夏作家之中尤其明显。域外学者之所以认可宁夏文学,认可宁夏“三棵树”,就源于在他们的创作中,看不到先锋小说那种充满灰暗气息和颓废情绪的书写,也看不到一些作家对“性”的近乎疯狂的渲染,对女性近乎野蛮的伤害与侮辱。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是关乎人类生存意义的探寻,是对真善美的鼓吹与呐喊,是对美好人性的礼赞。从谱系上看,他们继承了鲁迅乡土小说的批判性,又兼具沈从文小说的诗性与理想主义。放置于现代性的文化语境中,宁夏小说的这些特点的确在如此浮躁功利的社会风气中呈现出独有的价值与意义。评论者在研读宁夏文学时,更看重的是宁夏文学特殊的题材所展现出的精神价值。这一点在围绕石舒清小说创作的评论中得到验证。2001年,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获得鲁迅文学奖,2002年在《名作欣赏》第5期得到转载,2003年《名作欣赏》杂志发表了10篇关于《清水里的刀子》的专篇解读的评论文章。整合这些评论文章,发现这些论者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点集中在“终极关怀”这一哲学层面。小说的确涉及生死观的理解,老汉马子善在侍弄着一头待死的牛,实际上面对牛的过程是走向自己纵深的内心过程。看到牛的待死,想到自己的待死。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终极关怀是超越生死的基本路向。终极关怀正是源于人的存在的有限性而又企盼无限的超越性本质,它是人类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对生命本源和死亡价值的探索构成人生的终极性思考,这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哲学智慧;寻求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以化解生存和死亡尖锐对立的紧张状态,这是人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只有终极关怀才能化解生存和死亡、有限和无限的紧张对立,才能克服对于生死的困惑与焦虑。终极关怀是人类超越生死的基本途径。再加上石舒清的回族特征,信仰伊斯兰教,众多域外论者将小说生死观的解读与作者的宗教意识相联系,将“终极关怀”推向一个彼岸世界中去,“朝圣”“抵达天堂”“宗教仪式下的人性与神性”“生命的思考与终极关怀”“哲学意蕴”等,一时间一篇短篇小说承载了众多的意义,这也许连作家本人也没有想到。实际上对作者本人而言,他关注的的确是回族民间传统的精神,但绝非要将这种精神推向“终极”。石舒清自己就说道:“我不想说‘终极意义’一类大词,也不愿用‘拷问’一类说法逼迫自己,使自己难堪。”
再说了,一篇短篇小说如果完全是在宗教理念驱动下完成的,那么这篇小说肯定因为“理念先行”而失去文学上的价值。《清水里的刀子》之所以获得鲁迅文学奖而被方家认可,不仅是因为小说里所蕴含的宗教因素,如果仅仅是宗教因素,那么小说的深刻主题意蕴就被简化了。“宗教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不能以此作为整体的名称”。小说被认可,更重要的是观念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因素。穆斯林归真复命的文化心理是小说价值所在。可以说“终极关怀”是小说的果,小说的因则是民族的文化心理。石舒清的小说创作一直坚守民族文化传统的礼赞,众多评论文章在论及石舒清小说的精神价值时往往事先进行一个背景的预设,那就是石舒清的家乡———西海固。西海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但就是这样贫瘠的地区却养育着成千上万的西海固人民,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出了众多知名的作家。他们在消费本土化的经验,实际上也是在享用本土化的经验,是这片土地赋予了作家创作的灵感来源。西海固的苦难造就了西海固人精神的坚忍。石舒清是这种精神的鼓吹者,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回族老人与妇女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总是能够展示出不因苦难而丧失尊严的精神。回族学者马梅萍在《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论石舒清笔下的女人》中,梳理了西海固不同的女性形象,并指出赞母失父的潜在情绪构筑了西海固的群体人格:“西海固如一个自尊的未成年人一样在忧伤中思索自我、探寻终极关怀”。回族评论家白草更是不吝溢美之词,称赞石舒清小说集《暗处的力量》是“一个精神充盈的价值世界”。精神价值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了作家的创作题材和描写对象,石舒清小说的乡土地域本色与宗教情怀使评论者集中在“坚忍”“自尊”“关于心灵、关于生命的‘诗意与温情’”等这样的概念阐发上。
对于陈继明和金瓯而言,他们小说所彰显出的精神价值又是别样的表现方式。陈继明的小说侧重于“在平庸的精神废墟上寻找灵魂栖居的天堂”。陈继明的小说也谈生死,在他的长篇小说《一人一个天堂》之中,也写到人物的死亡问题,但小说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去描写死亡,其意义就不是“终极关怀”这样的概括所能界定的。由于潜在的政治话语所构成的文本内部的冲突,使得小说表现出一种解构与否定的精神,“《一人一个天堂》中的终极意味,就是取消终极”。陈继明小说往往表现出不堪的现实图景,但不堪只是表面,陈继明积极努力正是要追问不堪现实图景下人的救赎问题。学者赵炳鑫分析陈继明的小说后得出“文学的精神和价值维度要有形而上的意义建构,要体现文学的终极命题:爱、悲悯、宽恕、拯救等”,而“爱、悲悯、宽恕、拯救”也正是陈继明小说所反映出的精神价值。金瓯的小说被李兴阳在《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归在“西部先锋小说”之中,金瓯的写作受福克纳、塞林格、菲茨杰拉德等美国先锋作家的影响,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真正的先锋是精神的先锋,李兴阳认为金瓯等作家是“西部最有先锋精神的先锋作家”。按照学者谢有顺的说法:先锋就是自由。金瓯在小说创作中,追求的就是自由。只不过在具体的写作中,这种自由的精神是通过叙事表现出来的。郎伟就指出金瓯的小说《前面的路》“是一篇言说‘寻求自由’话题的小说”。金瓯借鉴现代派的艺术表达方式,通过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追求自由化的精神价值。在评论者看来,金瓯自由精神价值的建构是内化于小说的文本形式。但实际上,对于小说而言,形式与内容又是统一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指出:“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所以,细读金瓯的小说,那种“别一样的叙事方式”与小说中的那些狂妄不羁的人物统一在一起,建构出了金瓯所要表达的先锋精神。
三、语言艺术的自觉与小说文体的审视
最近几年,关于文学本体的讨论一直不断,原因就在于对文学认识上有众多的分歧,有的作家与学者认为,文学一定要兼具社会学、哲学的意义才够深刻,而有的则认为,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要尽量还原文学的艺术品质。其实,关于文学的多种认识都存在合理性。但不可否认,文学毕竟是一门艺术,一门审美艺术,更确切说是一门关于语言的审美艺术。汪曾祺先生就强调: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当下“作家论”的写作日渐形成一种范式———“题材”“主题”“艺术特色”,因此艺术特色的研究是当下作家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样对于宁夏“三棵树”的研究,也脱离不了这样的常规范式。从艺术的角度看,宁夏“三棵树”的小说确实呈现独特的艺术面貌,形成各自独有的艺术风格。作家张贤亮曾指出:陈继明的文风是冷静的客观的,甚至克制的,他常常故意把戏剧性降到最低点,石舒清非常善于写细微的东西,他的作品中常常充满了诗意和温情,金瓯的笔调则是极为强悍的、激越的。他们的风格不同,对他们的区分最终都是要通过他们的文本语言来实现的。石舒清在小说语言的加工上可谓颇具匠心,在石舒清的评论中,众多论者都被石舒清的小说语言打动,在论者看来,石舒清的小说语言已经化为作家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行为。申霞艳认为,石舒清的小说语言与内心世界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甚至语言能够主宰人生的片段。“语言是通向内心的幽径,语言呈现内心。每颗心都是一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暴露观点,作者、叙事者和人物无一例外。”
由于对鲁迅作品的执著偏爱,石舒清的小说语言不免受到鲁迅的影响。达吾则指出“石舒清的语言越来越有了鲁迅那种苍凉荒疏的品质,暗藏的热情,悯柔的忧伤,力透纸背的精确和不可复制的隐喻”。石舒清的小说“用平淡、质朴的语言,从不运用那些修饰性很强的语言”。这要分开来看,在石舒清小说的“日常叙事”中,语言风格一般比较平实,一旦卷入“死亡叙事”,语言则内敛沉郁,多暗示,多情味,富有张力。陈继明的小说语言“平淡、清雅、舒缓而又具解析力、口语化”。有些小说如《青铜》,语言则显得冰冷,似一种零度情感式的写作。这是陈继明在语言上的尝试,麻木的语言背后是陈继明一颗充满温暖的爱心。金瓯的小说语言经过多年的摸索与调整,逐渐形成自己的语言特色。“金瓯小说的语言运用正越来越强烈地呈现个人风格……读者在其小说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想要追求一种洁净、硬朗的语言风格特点,力图在相当节制的叙述中传达更为深厚的语言内涵,在有所遮蔽中释放更多的能量。为此,他信手拈来‘陌生化’等语言手段,并且创造了一些佳句”。这是为数不多的对金瓯小说的语言进行专门评论的文字。追求“陌生化”的语言表达,也是先锋派作家常用的艺术技巧。
按照陶东风的定义,所谓“文体就是文学作品的话语体式,是文体的结构方式……文体是一个揭示作品形式特征的概念”。根据文学创作的常识,一般创作成熟的作家都有着非常自觉的文体意识。宁夏“三棵树”在长期的创作中,业已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文体也是众多论者研究兴趣的一个集中点。然而对论者而言,对文体特征的揭示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章节去加以深刻阐释,因为小说文体的研究往往在艺术分析过程中得到零星的呈现。即便如此,对于宁夏“三棵树”而言,其小说文体特征得到了相应的阐释。论者普遍认为,石舒清的小说具有散文化诗化的特征,情节的淡化、叙述的抒情化、结构的散文化、小说思维的抽象化。获鲁迅文学奖的《清水里的刀子》更是集大成之作,体现出“简洁中的丰富”。石舒清的文体深受现代乡土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废名、沈从文等小说的诗化特征,在石舒清的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另外,石舒清小说所表现出的“地域化乡土风俗人情”的内容决定了其小说形式要相对舒缓诗化。论者认为,陈继明的小说侧重于心理冲突描写,被称为“陈继明式的情绪骚动”。陈继明的小说善于挖掘在当今社会现实下人物内心之间的心理冲突及隐秘的心理动机,所以陈继明的小说在形式上更观照人物的心理描写。论者称金瓯的小说为“没脑子”的小说,是因为金瓯的小说带有明显现代主义风格,碎片化、寓言体、拼贴、陌生化等形式无疑不是现代主义常用的表达方式。在《鸡蛋的眼泪》中的“寓言体”表达,在《前面的路》中的“陌生化”的语言,甚至在金瓯的其他小说之中,先锋的姿态决定了金瓯的小说不会循规蹈矩,不会受现实主义的羁绊,于是在小说的形式上也呈现出先锋的姿态。
四、文学批评的距离与历史语境
近些年,随着陈继明离开宁夏远走珠海,石舒清的小说写作断断续续,精力多集中在随笔的写作上,金瓯停笔后也已经逐渐淡出文学的视野。随之而来的是,对宁夏“三棵树”的关注度较之世纪初已经大大降低。前面的论述也是基于前期对他们的评论,纵观这些评论文章,虽然有些文章表现出较为深刻的见解,但由于评论的圈子化、地域化问题,批评因缺乏必要的距离而流于平淡,这一点在域内论者对石舒清的评论中比较明显。由于对民族文学有着浓郁的历史认同感,所以面对批评对象时往往因民族情感上的认同忽视了必要的问题意识。在大量的论述中,几乎找不到对石舒清创作进行批评的文字,究其原因是因为对批评对象的强烈认同而失去判断能力。比如回族评论家白草是一个文本细读的高手,对于张学东、季栋梁的某些小说都曾提出过批评,可是面对回族作家石舒清时,大都是赞美的文字。实际上,在对待自己本民族的文学文本及批评对象时,要在思维的理念和方法上拉开自己同本民族文化、文学精神的距离,以免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这时需要评论家作为一个“包厢里的观看者”去对民族文学的文本及批评对象做出相对客观、辩证、准确的阐释。萨义德曾说: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学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实际上,文学批评也是如此。
整合宁夏“三棵树”的评论,还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大量评论没有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去做出判断。要么,论者拘泥于封闭的文本进行阐释,从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等方法入手分析文本。要么,对文本进行社会学的批评,但在批评时却离开真实而丰富的社会语境。从批评的理论资源来看,不谈“现代性”是宁夏“三棵树”评论的一个短板,没有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使得评论缺乏应有的社会历史语境。面对小说文本之中人的生存危机,评论往往陷入失语的状态。因为论者没有真正意识到小说文本内外的冲突,文本内的人是诗意的,有坚忍的精神和尊严,可是文本外的社会现实却不是如此,也就是小说内的诗意人生与小说外严酷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论者没有借鉴现代性有效的理论资源对小说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审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论者的论述与作家的文本是契合的,但与社会现实却是断裂的。当然,对于评论者而言,还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的丰富与深刻,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让文学批评真正成为阐释性的批评,能够把宁夏“三棵树”的作品的价值最大化地阐释出来。
作者:许峰 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
- 上一篇:文学批评的建构主义探讨范文
- 下一篇:皖南民俗文化发展建议范文
精品推荐
- 1文学与文化论文
- 2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 3文学专业论文
- 4文学价值论文
- 5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 6文学作品分析论文
- 7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利与弊
- 8文学作品论文
- 9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 10文学写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