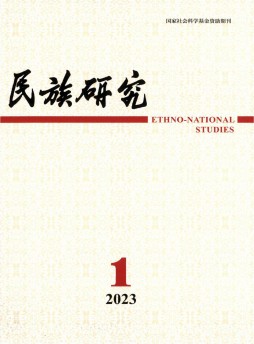民族新问题范文

1991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且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没有战争和外敌入侵的情势下自行解体,令世人震动和沉思。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苏联解体的根源进行了多方面探究,观点纷呈,智仁互见。总体上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社会危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意识形态诸方面)总爆发的结果。笔者也持此观点,但笔者不同意有的论者所说:“至于苏联的瓦解,也不是如同某些苏联新问题专家所言,是导因于境内的民族紧张情势,虽然这的确一直是苏联的隐忧之一。促使苏联瓦解的真正关键,应该是它所面临的经济困境。”[1]“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公布独立——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2]笔者赞同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和日本学者谷烟良三早在苏联解体前所提出的观点,前者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新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新问题。像它所继续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新问题的死胡同。”[3]后者强调,“民族新问题已成为左右苏联对外行动的危险因素,也是从内部动摇苏联体制的一个严重的政治新问题,假如处理不当,将会导致苏维埃帝国的崩溃。”[4]的确,苏联解体虽由多种因素所致,但民族新问题是一个起关键功能的深层次的因素,值得进一步探索。
一
苏联是在沙俄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因而,苏联民族新问题由来已久。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使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为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和奴役,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被迫俄罗斯化,并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厚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5]。十月革命虽然打坏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旧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民族新问题却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苏联党和国家为解决民族新问题作了不少努力,也曾取得一些成绩,但由于历史上传袭下来的民族新问题的严重性和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加之苏联在处理民族新问题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使民族新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苏联存在的70年中,其民族新问题可谓头绪纷繁、盘根错节,大致可概括为四种类型。
一是俄罗斯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矛盾。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约占苏联总人口的50略强,多数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境内。由于历史原因,也有不少俄罗斯人散居在少数民族地区。据统计,俄罗斯人在14个非俄罗斯共和国的人口中平均占19。俄罗斯民族同当地民族的关系遂成为一个突出新问题。俄罗斯人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占领军”、“殖民者”,而俄罗斯人则感到愤怒,认为俄罗斯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吃了亏还要挨骂,这是不公平的,因而从1990年起,《俄罗斯文学报》等报刊发出了要求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
二是加盟共和国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内,除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外,在非俄罗斯民族中也存在着由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一再要求把摩尔达维亚语定为国语,并把摩文的斯拉夫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该共和国议会已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这又引起当地讲俄语的居民的反对,他们纷纷组织罢工抗议。摩尔达维亚境内的加告兹族人总数只有16万,可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他们也害怕自己的语言被摩语同化,因而也集会游行,要求成立加告兹自治共和国。此外,有些民族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当局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虽然苏联宪法规定,根据各少数民族人数的多少和其他条件分别成立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加入所在的加盟共和国,并且通过加入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形式加入苏联,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却要求脱离加盟共和国。例如,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境内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都出现了要求脱离格鲁吉亚的集会游行。
三是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较大的民族为主,伴之以其他民族而组成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实际上就是民族之间,由于历史积怨、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而存在着矛盾。如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有关克里米亚半岛、科利沃尔斯、顿巴斯地区的争端;俄罗斯和哈萨克之间有关坚季兹湖地区大片领土的争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之间有关威特比斯州3个区、哥美里州6个区及斯摩棱斯克州的哥列茨基等地区的争端;俄罗斯和爱沙尼亚之间有关普斯科夫州的楚德湖和纳尔瓦河地区的争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之间有关撒马尔罕和布拉市的归属新问题的争端等等。这类民族矛盾最典型的是南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共和国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新问题而出现的武装冲突。1987年秋,阿境内主要由亚美尼亚族组成的纳卡州认为本民族遭受歧视而提出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加入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要求,得到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而遭到阿塞拜疆的果断拒绝。阿塞拜疆人涌入纳卡州,和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6名亚美尼亚人和6名阿塞拜疆人死亡,近200人受伤的流血惨案。苏联中心政府调动军队制止了冲突。1988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拒绝亚美尼亚的要求,同年7月12日,纳卡州苏维埃投票决定脱离阿塞拜疆共和国,苏联中心政府和阿塞拜疆均不予认可。此后,阿、亚两族之间的敌对活动不断升级,冲突亦蔓延至其他城市。1990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部分冲突严重的地区处于紧急状态,并派苏军和内务部队赶赴当地恢复和维持秩序。此后局势非但没有根本好转,矛盾反而加深。1991年苏联解体后,纳卡州归属新问题遂成为阿、亚两个独立共和国之间的争端。表面上看,这属于领土之争,而实质上,围绕这一新问题的矛盾却发展为把矛头指向中心、反对苏维埃、要求退出联盟的政治斗争,而且,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冲突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采取了武装暴力的方式。
四是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心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表现为加盟共和国争取自主权和要求独立。最为突出的是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这三国虽是小国,但地处战略要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和北欧国家相近,在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和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是根据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而并入苏联版图的。并入苏联后,由于受全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各共和国之间“平调”政策的影响,三国发展缓慢,和北欧诸国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三国认为,并入苏联给他们造成巨大不幸。于是从1987年起,每年的8月23日三国民族主义者都在各自的首都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打出以前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旗帜,谴责苏德条约及其秘密议定书导致了苏联对当时独立的三个共和国的占领,要求更多的自主权,直至脱离苏联。1989年8月23日,这三国利用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示威活动,示威者手拉手组成了连接三国主要城市,长达650公里的人链,表明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决心,煽动起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特征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而且三国协调行动、步调一致,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不过斗争的方式和前述纳卡新问题不同,没有发生武装冲突,而是以集会、示威、游行、立法等和平途径为主。
二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民族新问题,而只有当这些新问题尖锐激化到无法解决的地步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统一。苏联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苏联民族新问题激化并进而导致了联盟的解体?不少学者认为,其源盖出于戈尔巴乔夫推行错误的改革和国际反动势力起了推波助澜的功能。但笔者认为,比较而言,下列因素更为重要。
(一)背离联邦制原则,实行高度中心集权制,加深了各共和国和联盟中心的矛盾。苏联的国家体制采用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时由俄罗斯联邦、南高加索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4个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组成,这4个加盟共和国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的名称来命名的。1924~1940年,苏联发展成为16个加盟共和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时是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这15个加盟共和国的国名也都是以一个主体民族的名称来命名的。苏维埃联邦制是列宁的一大创造。十月革命前,列宁一直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建立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采用联邦制是历史的倒退,因而反对建立联邦制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国内外出现十分尖锐和复杂的形势,列宁改变了原来的主张,转而认为建立各苏维埃共和国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是适宜的。因为列宁看到,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过程中,被压迫民族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建立了各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情况下,若再坚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就易使少数民族产生误解和不信任,加之协约国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联合武装干涉,如不建立各民族联合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就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行联邦制的条件下,列宁还非凡强调两点:其一,为体现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各苏维埃共和国应以完全平等的主权国家自愿联合组成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各共和国实行民族自决,有加入和退出联盟的权利。其二,联邦制是向民主集中的单一制国家的过渡形式。但从斯大林开始的苏联领导人却片面理解列宁的联邦制思想,把建立联邦制国家看成仅仅是为解决当时复杂民族新问题的权宜之计,利用列宁有关联邦制是向集中制过渡形式的观点作为实行中心高度集权体制的依据,从而背离了联邦制原则。从表面上看,1924年、1936年和1977年的苏联宪法均重申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的精神,明确规定苏联是各主权苏维埃民族共和国的联盟,苏联保护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利(典型的是联合国成立时,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并且长时间在联合国派有外交代表),并可以自由退出苏联。这种双重主权国家的规定,在世界上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似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很大。而实际上,从1922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可以自由退出苏联,而加入苏联的共和国也不全是自愿的,如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以及完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三国加入苏联就是非凡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至于宪法赋予加盟共和国所享有的独立行使经济、财政、内务、司法、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检查监督和民族事务等方面的权利,也几乎是有名无实的。因为,列宁去世后,斯大林违反了列宁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逐步加强了个人集权地位,形成了党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同时,斯大林又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内高度集权集中的组织领导体制推行到国家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权集中的国家体制。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进行了改革,但并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高度集权集中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联邦制原则名存实亡。在经济上,联盟中心通过由它直接管理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控制了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企业和资产。如斯大林时期,联盟部所属企业占全苏工业总产值的89,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只占11;赫鲁晓夫时期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7,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3;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联盟部及联盟——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94,共和国部所属企业占6[6]。更有甚者,共和国连修建200张病床以上的医院或投资400万卢布以上的项目的权利都没有,而联盟中心在共和国修建新项目都可以不经共和国批准,也不同共和国商量。这不但造成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使共和国利益受到损害,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共和国的积极性。这种僵化而非弹性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讲不利于苏联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把大多数加盟共和国推向一个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要么是被强行地留在苏联,要么是一有机会就彻底摆脱联盟。而且不管多么有名无实,苏联的成立宣言、联盟条约以及历次宪法所公布和赋予的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及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权,还是为民族分离和独立运动提供了合法理论依据,从而导致联盟的解体。
(二)在理论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过早地公布民族新问题“已经解决”,导致民族关系中的消极现象日益增多。历史实践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到完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加之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需要逐步发展和完善,这就决定了在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新问题也将长期存在。
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对民族新问题的熟悉,都未能达到列宁所达到的高度,他们在民族理论上一直存在“左”的倾向,这同苏联领导人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熟悉有密切联系。他们总是抱有不切国情的超前熟悉,不是盲目地公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或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民族进程和社会进程是同步的,因而民族新问题必然随着社会进入高级阶段而不复存在。具体而言,1936年斯大林公布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建成了社会主义,不久,联共(布)十八大进一步公布,苏联已完成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因此,在民族新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制造民族纠纷的主要势力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心理和燃起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真正兄弟合作的关系”已建立起来了,“苏联各民族和种族,在全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根本谈不到民族权利会受到损害。”[7]甚至认为苏联各民族“已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以一种坚固的友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苏联“已经成为全世界真正民族平等和合作的榜样和典范”[8]。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1961年赫鲁晓夫公布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在这个条件下,“苏联已经解决了人类世世代代所关心的,而资本主义世界直到现在仍然尖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新问题,即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新问题”,因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9]同样,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正在向共产主义转变,因而“民族新问题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了。”[10]可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对苏联民族新问题状况都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就连提出各种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也未能跳出上述观念的圈子,在其《改革和新思维》一书中很少论及民族新问题,在民族理论上基本步了前任之后尘。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苏联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各民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对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已得到确立,并已进入亿万人的意识之中。苏联人民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成的。”[11]正是由于苏联领导人对本国民族关系发展状况的错误估计,忽视民族新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因而苏共总是对实际存在的各种民族新问题熟视无睹,报喜不报忧;总是强调各民族的共性而无视其个性,人为地加快各民族接近和融合的进程。这样,旧的民族新问题被人为地掩盖起来,得不到及时解决,而新的新问题又积累下来,新旧矛盾交织,一旦总爆发就必然危及国家统一。
(三)民族政策失误引起族际关系紧张。正确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对民族关系状况及各民族间主要矛盾的正确估计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列宁之后的历届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新问题的解决估计太高,严重脱离实际,因此在民族政策上必然会出现一系列失误。苏联民族政策失误主要表现在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新问题和维护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两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和阶级、民族新问题和阶级新问题是两类不同的概念,虽然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能将其完全等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新问题一般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通过宣传、教育、疏导、协调等方法妥善加以解决。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却忽视民族新问题和阶级新问题的区别,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任何谋求本民族利益的努力不加分析地斥之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新问题。30年代初,苏联不顾少数民族的非凡性,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使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等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因饥荒而死亡500~900万人[12],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斯大林将他们打成民族主义危险分子,流放和镇压了大批农民和富农。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非凡是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多数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因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而遭到清洗和镇压。如1937~1938年间,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心第一书记皆被处死;哈共中央局成员全部被杀;1937年5月,出席格鲁吉亚共产党十大的644名代表,会后不久竟有86被捕、流放或遭监禁。卫国战争时期,借口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和法西斯勾结而背叛祖国”,就把克里米亚鞑靼人、德意志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11个弱小民族的大约500万人赶出其世代居住地,强制其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等条件艰苦的地方,其中有几个民族在赫鲁晓夫时期恢复了名誉,返回家园,恢复了自治,而另3个民族,后来虽也恢复了名誉,但未允其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因而留下动乱的根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仍然坚持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的观点,并且认为国内民族主义活动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将各共和国内不满苏共政策、要求扩大自主权以及歌颂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统统当成资产阶级分子,大加批判或监禁,把不满和反抗的少数民族作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进行打击和镇压。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民族新问题,其结果是在民族关系中人为地制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属于各民族间的内部矛盾人为地转化为敌我矛盾,造成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严重伤害了这些民族的感情,加深了民族关系危机,助长了民族分离倾向。
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作为旧时代的糟粕,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理应予以清除。列宁果断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如大俄罗斯主义和各种地方民族主义,他要求着重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妨碍实现各民族平等和团结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公布“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13]但列宁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忽视了列宁的教导,虽然他们一直笼统强调反对民族主义,但实际上着重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维护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第一,歪曲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把沙俄的侵略扩张说成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是少数民族的“自愿归并”,沙皇给被征服民族带来“文明和进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认为在二次大战中苏联恢复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等地区,强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摩尔多瓦四国加入苏联,收复库页岛及千岛群岛,“这样的边界最符合苏联历史的真实”[14]。在斯大林看来,凡沙俄帝国占领过的领土都应该是苏联的领土,强占这些地方是恢复苏联“合理的边界”。这实际上违反了苏联成立之初列宁制定的有关不答应划分势力范围的对外政策原则。第二,任意吹捧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的伟大民族和领导民族,无视其他民族的地位和贡献。如他们宣称俄罗斯是各共和国联合成统一国家的“中心”,吹捧俄罗斯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苏联各民族的母亲”,“是俄罗斯人帮助其他民族克服了几百年的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15]。甚至在1989年9月苏共民族政策纲领中仍坚持要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新联盟国家,继续强调“俄罗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整个联盟国家的凝聚力量,对于克服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6]。第三,俄罗斯人在政治上享有特权。1923年6月,按斯大林在全苏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选举原则,苏联中心执行委员会由350名代表组成,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代表为280名,占80,而其他3个共和国代表只有70名,仅占20[17]。在历届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中,虽然各民族共和国都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但历届国家元首则大多为俄罗斯人,历届苏联政府首脑除斯大林一人外都是俄罗斯人,至于联盟中心政府各部委主要领导职务也大多由俄罗斯人担任。在实际上直接掌控国家最高权力的苏共中心领导机关中,虽有少数非俄罗斯人参加,但除斯大林外,其余各届苏共中心最高领导职务均由俄罗斯人担任。典型的例证是,安德罗波夫为首的10人组成的中心书记处全部是俄罗斯人;各主要民族共产党员占全体党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俄罗斯59.8、乌克兰16.02、白俄罗斯3.76、乌兹别克2.31、哈萨克1.94、格鲁吉亚1.68、阿塞拜疆1.65、亚美尼亚1.51、摩尔达维亚0.53。上述做法,严重违反了各共和国和各民族平等的原则。第四,强制推广俄语并作为苏联的国语,歧视少数民族语言。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多民族国家里,语言政策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任何民族语言的任何歧视和限制,不答应任何民族语言享有任何特权,认为假如把一个大民族的语言强加给其他民族,势必造成人为地实行民族同化政策。列宁指出:“谁不承认和不维护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不同一切民族压迫或不平等现象作斗争,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民主主义者。”[18]他坚持民族语言平等,反对强行推广俄语,他指出:“用棍棒强迫”其他民族学习俄语,其后果只能是“使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难以为其他民族集团所接受,主要是会加深敌对情绪,造成无数新的摩擦,增加不和和隔膜等等。”[19]但列宁之后的历届领导人都违反民族平等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广俄语,力图使俄语成为各共和国国语。据统计,1986年苏联出版发行各种书籍22亿册,其中俄文书籍占86,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书籍仅占14(少数民族人占全苏人口49.2)[20]。有几十个小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处于消失的边缘。
几十年来,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纵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民族平等原则,事实上使俄罗斯处于联盟中心领导地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享有特权,而其他少数民族则处于附属的“次等民族”地位。民族不平等现象的长期存在,激发了少数民族对联盟中心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严重不满情绪,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普遍存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互为因果,成为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 上一篇:乡镇人大总结范文
- 下一篇:乡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总结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