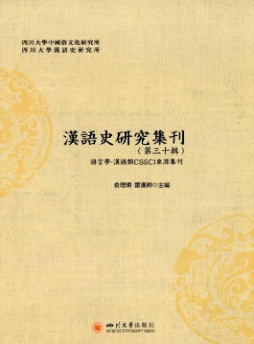谈汉语文学传统性格范文
时间:2022-07-25 09:47:58

一、文学与传统
宗白华先生曾道: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形重要。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1](P68-69)。今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另一个转折点时,对中国心灵幽情壮采的追溯,对民族文化的自省,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有反观,才会有前瞻;有探求本源,才会有一往无前。欧洲文艺复兴打着复古的旗号,成为世界艺术长河中登峰造极的典范。中国也素有“诗必盛唐,文必秦汉”之复古情怀,风骚并举、魏晋风骨由此成为历代文人发远古之深思,求原始之拙朴的范本。笔者认为,这必然是引领文学复兴的强大力量。在中国文化的链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串闪烁着精神之光的文本,证明文字从来都不是无能的,文字勾勒的历来都是让人感觉到回归与诗意的东西。《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行前10位的大师们,充分体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鲁迅以其呐喊、呵斥表达他忧国忧民的情怀;沈从文则以其与世无争的边城话语表达其否定之否定,作一种间离;老舍是彻头彻尾的悲凉;张爱玲的飘然出尘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文体中、生活中、性别中、喜好中、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传奇中;钱钟书的“围城”更是困处愁城的中国文人之绝佳比赋;茅盾恢宏文字,审视着芸芸众生之狱与欲;白先勇叙述一种文化的繁华、衰落、消失以至无法挽回的段落,将历史归结于全然的记忆之中;巴金的忧愤是显而易见的控诉与反抗;萧红以独特的地域色彩、地域风俗和厚重的基调点染出凄凉而苦难的人生;刘鹗则以中国文字对家与国实施补救之理想。从以上这些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深烙印。尽管当前的文学创作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可我们也无须惊慌。任何一种潮流皆以混沌为其初始,并以另一种混沌为其终结,这是人类文明的必然轨迹,不到尘埃落定的前一秒,我们都不知道文字的指向是此岸抑或彼岸。可不管是此岸抑或彼岸,都一定会附着着专属中国人和汉语文学的个性特征,这有几千年的传统国文为证。这不,我还在写,都还在写。对汉字的书写依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种人生态度[2](P83-90)。
二、儒道兼善的文化性格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源头,在漫长的中国文化的积淀过程中,文学以诸多文艺形式之先行者的姿态,吸收与呈现的皆是最地道、最全面的传统精髓。若然将传统文学作一比,笔者认为,它是在抑压与释放交织中、在雅与俗之间穿行着生产出来的怪胎;它是儒与道逆向纠缠中催生出来的“恶之花”;它有着儒家思想的父系宗亲,又有着道家学说的母系血液。因此,它以独特的面目放射出惊世之光,体现着整个民族生活的精神质量。
1.兼济天下的忧患意识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文学早已形成了一套不可逾越的泛道德系统,即文以载道的功利观,人格重于文章、道统重于文统的为人为文准则,“诗言志”的文学观,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主题,以善为美的思想,忧患意识,人民性等等。文学不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就是“兴起其好善恶之心”[3](P67-70)。《论语》云:“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中庸》又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P177)这种儒家的天人合一观肇始于人对宇宙的根源感,而这又是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终极元素———忧患意识的源头,它充满了主体性和道德性的人文精神,这样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字里面已被弘扬至淋漓尽致的地步。战国时期,楚人屈原在《九章•涉江》中写道: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5](P158-159)此间抒发了他离乡去官之后仍念念不忘替朝廷时政忧心之情。尽管自己追求高洁理想,是“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但对国政却终究未能释怀,处处体现出他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情感和对“美政”的追求。汉魏时期有以史喻今明志的贾谊、司马迁,有反映民生疾苦的建安三曹七子。曹植在《白马篇》中描写了“少小去乡邑”的“幽并游侠儿”们为国捐躯、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捣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各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6](P77)唐人诗歌中的爱国主义诗句更是俯拾皆是:李白有“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避日,长安不见使人愁。”[6](P100)让我们再看看李白、骆宾王、杨炯、王维、王昌龄的五首同名诗[1](P294、295、298、299):《从军行》(李白)从军玉门道,逐虏金微山。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从军行》(骆宾王)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从军行》(杨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王维)吹角动行人,喧喧行人起。笳悲马嘶乱,争渡金河水。日暮沙漠垂,战声烟尘里。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从军行》(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当然,最广为人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名句还要算诗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7](P299)宋代亦不乏忧国忧民的代表作品:《关山月》(陆游)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此外,传诵千古的还有辛弃疾的《水龙吟》和岳飞的《满江红》。明清时期的爱国忧愤诗文总体而言逊于唐宋,但犹有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依然表达出不离不弃的爱国情感的惊世之句。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无异于“平地一声惊雷响”,是“忧国忧民”在封建制度没落之时转向讽刺、谴责甚而喝斥、呐喊的标志之一。
2.超然物外的追求
同时,我们看到,影响中国传统文学架构的还有另一股力量,即返朴归真、崇尚自然的生活理想;质朴、含蓄、冲淡、清奇的文本追求;“童心”、“性灵”的文学观;“妙悟”、“意境”的审美范畴;泯物我、同生死、一寿夭、超利害、齐是非的人生态度;等等[8](P86-189)。道家重灵感、重天机、重精神的艺术追求看似是对儒家思想的反拨,实则它是古代文人对付实际生活的一种无奈对策。每一位读书人皆愿意通过读圣贤之书求功名、入仕途、安身立命、精忠报国。翻开中国的文人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页上都写着“怀才不遇”四个字。从屈原到贾谊、司马迁、曹植、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李煜,乃至欧阳修、苏轼、陆游、辛弃疾……,一串长长的名单,惊人的相似:所有人都是少年得志,而后英年早逝或郁郁不得志;所有人的创作几乎都可分为前后期,前期都意气风发,后期都愤慨哀怨。就算是屈原、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这些较能体现道家风范的文人,也没有几个是真正心甘情愿弃官从道的。似乎只有陶渊明算活得比较明白:一开始他主要是由于生活贫困而入仕,后自动弃官归隐(而不是被贬),此后再也没有过入仕的想法和举动,因而避免了多次被贬的命运。在他干净的躬耕自资的生活里,他写下了引人入胜的《桃花源诗并记》[6](P80),更写下了传唱千古的《饮酒》诗[7](P299):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作者陶然自乐,与世无争,流露出与大自然融合为一的美好追求。在“儒道兼善”的较量中,虽然儒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只有在欲儒而不能儒之时,文人们才退而求其次地取“道”弃“儒”,独善其身。然而,幸好有了这许许多多的意外,才给传统的文学注入了旷达、超脱的品质,才有了丰富奇诡、恣肆的道家风格。话又说回来,尽管择“道”是出于无奈,尽管在隐世出尘的文人中没有几人不是对积极入仕、兼济天下难以忘怀的,可在儒为主流的创作中,又有谁不是梦想着弃官归田、超然物外、任性而为的境界呢?历代文人就是这样在儒与道、出与入的对立与互补之间徘徊,中国文学的性格也由此变得丰富多彩。
三、顺天安命的乐观性格
中华民族是聪明的民族,所以在创造超然物外这样一套人生哲学之外,又创造了另一种顺应命运的手段,这就是乐观。与西方文化强调分离与对抗不同,中华民族强调的是乐安天命、贵和尚中、顺天而行。中国武术中的太极拳,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四两拨千金、以圆滑克锐利,便是这一精神的绝佳体现。日常生活中常说的“随缘”、“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等道理,到了艺术中就是要达到质与文、善与美、情与理的和谐一致,绘画要浓淡相宜,音乐要八音克谐,文字要虚实相生、形神兼备。这种性格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有两种表现形态:一是在喜剧作品中,乐观性格导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结局,如《摘翠百•小春秋》中对《西厢记》的结尾有如下描述[9](P230):之官千里赴西秦,满路花香喷,仙掌云开帝城近。沐皇恩,夫荣妻贵临亨运:七香车坐稳,五花诰墨润,永作玉堂臣。这种喜庆得有点俗气的尾巴,在优美动人的《牡丹亭》里同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腻得都有点与前文的“以意趣神色为主”的格调相去甚远。看第十出《惊梦》中的“游园”部
分,语言典雅清丽,情调楚楚动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10](P43)可结尾却变成:姻缘诧,姻缘诧,阴人梦黄泉下。福分大,福分大,周堂内是这朝门下。齐见驾,齐见驾,真喜洽,真喜洽。领阳间诰敕,去阴司销假滑稽是滑稽了点,离谱也是离谱大了,可观众就是这么期待的。王实甫、汤显祖如果不这么写也过不了自己那关,这是文化理想主义在民族戏剧中最原在的表现。而在悲剧作品中,乐观性格体现得更深刻和耐人寻味,由此也显得更巧妙更智慧。对于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对于厄运、死亡、离散等命运中不可扼转的巨大力量,中国人往往是在悲痛之余给予命该如此的平静解释,有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安心,《红楼梦》的结尾便是例证。
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情怀在现当代的作品中仍有强劲的后续力: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半生缘》、钱钟书的《围城》、白先勇的《台北人》、阿城的《棋王》、苏童的《红粉》、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陈忠实的《白鹿原》、李碧华的《霸王别姬》……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顺天安命性格的悲剧传承。中国传统文学的乐观性格不但有悲剧喜剧两种表现形态,而且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重性:一方面,它“积极入世,热爱生命,穷达皆能自处,宠辱全然不惊”;另一方面,它对“天意”逆来顺受,诚惶诚恐,自满、自欺,麻木压抑。鲁迅对于中国人的“乐观”早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是深挖“国民性”弱点和“精神胜利”病态的大师:“大概人生现实的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更使读者感着不快”。“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11](P316)。他所认为的“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胡适也有同感:“团圆快乐的文学是说谎的文学,它们只能使人觉得一种满足,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想反省。”[3](P70)我们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的顺天安命和乐观性格是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国民性之上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集体无意识。四、蕴藉写意的艺术性格儒道兼善、顺天安命的精神内核必然导致蕴藉写意的艺术形式。
诗人于坚曾这样描绘汉语:汉语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富于诗性的语言,汉语与世界的关系是抚摸的关系,汉语的性质是柔软温和的。把中国传统上的那些伟大的诗歌圣哲和他们的作品仅仅看成死掉的古董,这是一种蒙昧的知识。在我看来,它们———唐诗宋词,乃是世界诗歌的常青的生命源泉之一[12](P15)。中国古代文学的确不像西方文学那样充满着本能的冲动、狂野的激情和绝望的痛苦,也没能产生毁灭性的悲剧之美。至少,中国传统文学也是将冲动、激情和痛苦稀释、搅拌过后出之以温吞宜人的外表,等火气尽收之后制造绕梁三日之效果,并给悲剧的结尾加以糖衣包装,温柔敦厚、贵和尚中促生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贵族气,所以它是一种诗性的文学。“诗性”一词,似乎是中国文化中于事于人的一种无以上之的评价了。以“诗性”冠之的中国文学,其最早出现的体裁是诗歌,最兴盛最发达的艺术形式是诗歌散文,最常用的技法、最常见的风格是从诗歌里来的,最脍炙人口的篇章和形象皆存活于古诗之中。诗性的中国文学有着许多诗性特征:长于抒情;重写意不重写实,重传神不重摹形;小说戏剧也讲求诗情甚或用诗的形式表达,写得优美的小说戏剧被称为诗化小说戏剧;古代文论中的美学范畴也被诗气浸渍熏染,变得飘逸跳脱,“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韵”“味”“神”、“风骨”、“格调”、“意境”、“趣”、“情”、“气”、“品”、“妙悟”、“童心”、“性灵”……无一不诗意缭绕[3](P67-70)[13](P225-226)。又以《牡丹亭•惊梦》中的“游园”为例:[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好姐姐]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呖呖莺声溜的圆。[10](P43)《牡丹亭》成为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除却它的曲折剧情、典型人物,其优美生动、典雅清丽的诗化语言恐怕是功不可没的。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潇湘魁夺菊花诗,薛蘅芜夜拟菊花题”中,众人作菊花诗,《忆菊》《访菊》《种菊》《对菊》《供菊》《咏菊》《画菊》《问菊》《簪菊》《菊影》《菊梦》《残菊》共十二首,首首皆好,最后黛玉夺魁。众人你一言、我一句地评说,后热蟹来了,众人兴致更为高昂,又作了三首赏蟹诗。光是真正的诗作在此一回便有十几首之多,更不消说全书一百二十回从头至尾吟诗作对的总数,还有书中诗情画意的美景与心情,由此看来,《红楼梦》堪称“诗性全书”[14](P517-533)。谈到“诗性”二字不能不提到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他的《边城》充分体现了他的诗性理想:———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15](P234)———过渡人一看老船夫不见了,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绒,就明白那老的已作完了自己份上的工作,安安静静躺到土坑里给小蛆吃掉了;必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着翠翠,一面摸出钱来塞到竹筒中去。“天保佑你,死了的到西方去,活下去的永保平安。”翠翠明白那些有钱人的怜悯与同情意思,心里软软的,酸酸的,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从这小说的一头和一尾,我们看到,文章笔墨是淡淡的,一路道来,“并无风花雪月之妙,反而真切动人了”。这种平和幽远素净的深韵是沈从文对于中国人所谓“诗意”的见地。他的小说“是热情的,然而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6](P461)。
正是他的点到即止、他的白描、他的淡雅、他的留白、他潜在的“读者心态”、他对于现实生活的间离感,使他的小说充满了“诗性”。这“诗性”的气息遍布在原生态的古远山乡之间,遍布在文本的情节中,更弥漫于逐字逐句的话语中。达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境界,除了他本人天赋内蕴的功力,也有传统文化种下的慧根!以上所举只是小说、戏曲中诗性之事例,那么中国古诗中的诗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元人马东篱一首《天净沙小令》可为一斑而知全豹之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历代文人以不朽之作品灌溉了中国文学这一圣地,赋予其形象与生命。在这形象与生命之中有着以上论及的多重性格,印证着中国文人几千年的光荣与梦想,它值得我们深思与回溯。
- 上一篇:推行学校教科农建设意见范文
- 下一篇:教科农业开发方案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