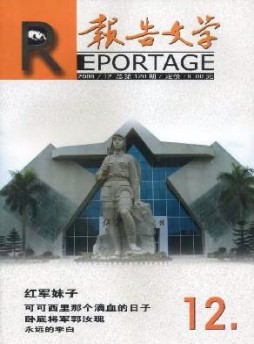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范文
时间:2022-09-28 11:5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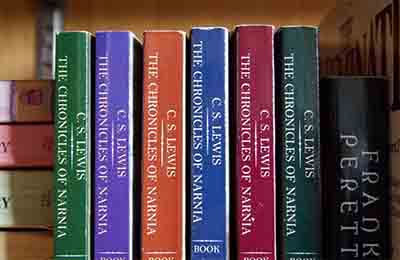
一、文学场中的《小说选刊》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他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提出了“场”的概念,并主张用场域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学领域。根据布迪厄的理论,所谓“场”就是一个“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1]。“文学场”就是一个遵循文学自身的运行和变化规律的空间。布迪厄强调,“文学场”并不是一个自我独立、封闭的体系,而是与政治场、经济场等共同处于一个更大的“权力场”之中。“权力场是行动者与机构之间的力量关系空间”,这些场域以及场域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静止的;相反,它们处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动态网络中。“文学(等)场本身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了一个被统治的位置”,经常受到来自“政治场”和“经济场”的挤压。这种“挤压”,不是通过外部发生,而是通过一种“折射”的方式来影响“文学场”的内部法则,即文学的“自主原则”。文学的自主原则是“文学场”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要素,它是建立在一种“颠倒的”经济原则———“输者为赢”的基础之上的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想化追求。
这种“挤压”具体反映到文学上,便表现为代表着“政治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原则”或代表着“经济场”的以大众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市场原则”试图以自己的标准取代文学的审美原则,重新建立起“文学场”等级秩序的过程。《小说选刊》作为中国作协主办的刊物之一,兼具大众传播媒介、官方意识形态载体和纯文学期刊定位的三种文化身份。自1980年创刊以来,它便一直以积极的态度在文学传播、文学评价和生产引导方面有力地参与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是当代文学场域中的一个重要“占位”,也是管窥当代文学场的一个重要窗口。事实上,中国当代的“文学场”一直处在与“经济场”和“政治场”博弈的过程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刚刚摆脱了“工具论”的文学在经历了“伤痕”“反思”之后开始向文学自我回归,先锋小说兴起。《小说选刊》也经历了一个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依附到渐具开放性、包容性、多样性的过程。1989年,《小说选刊》停刊,直到1995年才复刊。此时的《小说选刊》面对的是已经翻天覆地的文学环境和广泛流失的读者群。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开始加速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文学体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文化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而逐渐边缘化,文学传媒的生存环境也出现了重大转变。元气大伤的《小说选刊》由于1990~1995年这一发展进程的断裂,相比于其他的文学期刊,似乎错过了转型的最佳酝酿期与适应期。1995年,《小说选刊》开始自负盈亏。2005年,《小说选刊》的发行量陷入谷底,临近破产边缘。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小说选刊》大刀阔斧的改版以及对“底层文学”的推动,便具有了尤为重要的意义;同时,“文学场”的观察视域,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观察的角度与解释的可能。
二、底层文学:经济场与政治场的合流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初兴起于文坛的一股小说创作潮流,主要以城市贫民、农民工,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为写作对象,反映了他们在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的严酷现实中的生存状态,通常蕴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以及人道主义关怀。事实上,至今为止,“底层文学”仍是一个颇为可疑而尚无定论的提法,很大程度上,“底层”只是对当下中国正在形成的一个庞大的无名阶层命名的权宜之计,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当下中国的‘底层文学’难以被当作具有相应的艺术成规和美学范畴的文学来讨论,人们面对着的,其实是被‘底层文学’所指认、讨论者感同身受的社会思想状况。”[3]大约从2004年开始,文学期刊普遍表现出向底层叙事倾斜的趋势,特别是《小说选刊》,更是以大刀阔斧的改版方式参与到“底层文学”写作潮流的倡导与推动之中,尤以2006年和2007年为甚。事实证明,《小说选刊》选择“底层文学”来作为其改版之后力推的写作潮流,是经过颇为慎重的考虑的。一方面,“底层”热的兴起与国家话语的诱导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2002年3月5日,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首次以官方的名义使用了“弱势群体”的提法,此后“弱势群体”的问题便成为“两会”的焦点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也是“底层文学”兴起的重要背景。2001年,国家正式将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且于2003年正式将其写入工作报告。“三农问题”自此正式成为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此后又连年1号文件,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这种时间上的巧妙重合昭示了两者间的必然联系。事实上,“底层文学”中的一大半,描写的都是农民———或留守在黄土地上,或挣扎在城市边缘,或奔波在城乡之间。在“工业反哺农业”,贫富差距急剧增大的今天,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底层”的代名词。因此,《小说选刊》在此时对底层文学的大力提倡,可以说隐含着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意迎合。
实际上,常常以“国刊”自居的《小说选刊》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主旋律的呼应姿态。副主编冯敏在评论《我们的路》时写道:“在读大宝哥这个形象时,我很自然联想到那些耳熟能详的关键词:‘三农问题’‘一号文件’‘科学发展观’‘城乡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等等”[4];小说家徐坤在读者来信上也直言“改版之后的选刊,顺应时势,在坚持严选标准基础上,贴近当下、替农民和农民工代言的文章多了起来”[5];《小说选刊》改版一周年,主编杜卫东在接受采访时宣称:“《小说选刊》去年改版以来所倡导的文学主张,符合总书记对文学界的期待和要求。”[6]另一方面,底层写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它首先由于其“文坛热点”的身份成为精英文化圈追捧的“新宠”。同时,底层写作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绝对的道义资源,甚至等同于“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轻易博取了大众读者的同情心,而其创作对现实主义手法的偏爱,也贴合了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起开设“说话”栏目,从刊登的读者来信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那青年农民工简单的饭菜让我一震,而他脸上那无邪的、灿烂的笑,更令我震惊,那一刹那,我既想哭,又想笑……”(2006年第3期)“现实主义的作品仍然是我的最爱。”(2006年第9期)“封面设计贴近我们农村的生活。”(2006年第11期)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问题小说”开始,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强力打造”,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尤其对于我们这个务实,实践理性很强的国度,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要求,便倾向于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问题的揭示。读者希望的是文学能尖锐地提出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以利于他们的思考和行动,他们对于文学思想的要求,对于问题尖锐性的要求,胜过了对于文学艺术形象的要求。”[7]因此,《小说选刊》对“底层文学”的大力推广,可以说正好顺应了大众的审美规范。
由此可见,“底层文学”同时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读者的审美要求。经过两年对“底层叙事”的大力倡导,《小说选刊》在全国文学期刊征订数总体下滑的大背景下,却在定价上涨的情况下征订数不降反增,成功实现了对市场的突围。可以说,《小说选刊》正是充分利用了代表“政治场”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原则和代表“经济场”的以大众审美趣味为主导的“市场原则”在“底层文学”上“合流”这一特点,才取得了2006年改版的巨大成功。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将《小说选刊》此举看成是“文学场”中“文学审美原则”对“政治场”和“经济场”审美原则的全面投降。政治正确与经济正确并不代表着文学上的注定失败,有时或许仅仅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事实上,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小说选刊》在“利用”“底层”这个概念时,对底层叙事中出现的病象进行努力纠偏,试图维护“文学场”的审美自主原则,并建立起自己的审美领导权的过程。
三、审美领导权:文学场的自救
“审美领导权”一词是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来说明审美原则上的倾向。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描述了统治阶级不诉诸暴力或强制便能使从属阶级的意识得以构造的过程。具体来说,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是以市民社会广大民众“自愿的”同意为前提的,并且是以不断获取从属阶级的“同意”,进而达成统治阶级世界观指导下的“集体意志”为旨归的。他对于意识形态斗争方式的思考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小说选刊》自创刊以来,无论是在封面还是在言语之间,一直都有意或无意地强调自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官方身份以及在文坛的权威地位,宣称自己“所选的作品代表了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最新成果,全面反映中国小说创作面貌。历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十有八九都被《小说选刊》选载过,是当代中国影响力最大,最具权威性并拥有广泛读者的文学月刊,素有‘文坛风向标’和‘文学浓缩本’之誉,被称为‘小说国刊’”[8]。同时,它还通过一系列的实际行动来树立自己的“大刊”姿态,以“整个社会了解和瞭望‘文学’的窗口”自居。例如,每一期开设“全国报刊小说概览”,给读者造成“一刊在手,天下我有”的感觉;在年尾的时候不惜腾出多个版面为兄弟报刊刊发征订广告,表现出自己作为一个部级大刊应有的气度和魄力;当社会上发生重大事件时,《小说选刊》也总是积极响应,热心公益,并号召组织作家进行捐款,以打造自己文坛代表者的形象。《小说选刊》长期以来这样不遗余力地对自己的宣传也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很多读者“总在心中给它定位,认为既然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当然应该是同类期刊中最权威的,最好看的”[9]。在以一系列的言行直接标榜自己的权威地位的基础之上,《小说选刊》还通过对读者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建立自己的审美领导权。具体表现在对“底层文学”潮流的推动和引导中,《小说选刊》对“底层文学”进行引导并试图纠偏的努力。严格地说,“底层文学”体现了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密切跟踪,对弱势群体的体恤和关怀,尤其是对转型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形态及其精神走向给予了自觉的思考。但是,伴随着“底层无法被真正表述”的焦虑以及大部分作家对底层经验实际的疏远与陌生,底层写作从其创作实绩来看,一直“呈现出含混的庞杂和徘徊局面”[10]。特别是2004年以来,随着“底层写作”日益成为文坛批评界与创作界追逐的“热点”,“底层写作”渐渐由一种“关怀”变为一种“卖点”,并随之出现了许多病象。《小说选刊》在2006年改版以后就专门设置了“声音”栏目以“对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和病象进行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批评;对小说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倾向和思潮做前瞻性引领”[11]。两年间,《小说选刊》利用“声音”栏目,刊发了将近10篇有关底层文学的评论,如邵燕君的《底层如何文学》、李建军的《重新理解现实主义》、陈福民的《讲述“底层文学”需要新语法》、李云雷的《“底层叙事”前进的方向》、贺绍俊的《底层文学的社会性与文学性》、林希的《草根写作是文学创作的主流》和《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鲁太光的《我们为什么写不好农民》等。这些评论,针对底层写作出现的将底层妖魔化、苦难化、模式化的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文学性缺乏等弊病均进行了批评和引导。
除了借批评家之口来表达刊物的导向意图之外,《小说选刊》还往往直接发声,甚至为底层叙事开出了“苦难+希望”的药方,要求“关注生活中的苦难与罪恶,同时又主张在罪恶面前亮出正义的利剑,在苦难旁边点燃希望的篝火。”[6]除了每一期位于卷首语位置的“阅读与阐释”对重点作品的导读外,选刊还于2006年第3期开始为每一篇没有配专文评论的小说撰写“责编稿签”,以寥寥百余字言简意赅地对读者进行阅读提示。不难设想,每当读者打开书页或翻开小说,首先浏览到的是置于开头部分的“阅读阐释”或“责编稿签”,无形之中已经为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定下了基调。例如在2006年第3期的“阅读与阐释”中,提到叙述人贩子靠弄残儿童以其乞讨敛财的《坏爸爸》时,编者认为这篇小说尽管“铺展了可怕的残暴与苦难”,但“好在警察来了,好在很多人都在问这是谁的孩子?可以给一个回答: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能无动于衷吗?”又如同年第6期在提到马秋芬的《蚂蚁上树》时,编者直言:“马秋芬并非一味描写苦难,底层生活也有自己的形态,一分钟快乐都没有的底层生活是不存在的”,直接表明了对此类饱含温情的作品的肯定与偏爱。又如蓝石的《好日子》配以的“责编稿签”有言:“这篇小说在塑造底层人物时,有别于众多苦大仇深的面孔。”“下岗工人高健被引车卖浆者流视为窝囊废,可谓是底层的底层了,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整天一副没心没肺,乐天派面孔。”津子围《稻草》的责编评价:“清明已不再善良清明,初月却依然初守如梦———善比恶更有力量。”诸如此类的评述可谓比比皆是。由于这些栏目长期坚持开设,它们已经逐渐“内化”为了《小说选刊》内容的一部分。此外,《小说选刊》还通过内容编排上对“泪水”与“笑脸”的有意识平衡,封面内容选择上对希望与温情的侧重甚至直接向作家约稿的方式,来全面渗透和传递自己的导向意识。
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无产阶级“有机的”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进行教育的过程。就教育的形式而言,他反对强制的“灌输”方式,而是注重将教育与民众的自觉结合起来。至于教育的方式,可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即作文化上的长期渗透与瓦解。《小说选刊》在推广自己的导向意图时,采取的即是这样一种温和的“教育”方式。那一篇篇有意识选择的小说与评论,以及“阅读与阐释”“责编稿签”,实际上就是其宣传思想的一个个“阵地”,在“细无声”的“润物”过程中,将自己的价值导向传递给了读者,从而树立起自己的审美领导权。而广大读者(包括许多的小说创作者)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过程中逐渐接受《小说选刊》的价值导向,甚至将其转化成自己的审美无意识。例如2006年第8期刊登的一篇读者来信,该读者就直接宣称,尽管《我们的路》《坏爸爸》之类的作品能够让人潸然泪下,但若“能选些催人奋发向上的社会感、责任感强烈的激励人生的小说就更可口了”!在文化领导权获取的问题上,葛兰西谨慎地提出要考虑从属阶级的利益,他认为:“毫无疑问,领导权成为事实的前提,就是需要估计将被施加领导权的那些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就是需要通过妥协形成某种平衡。换言之,就是需要领导集团做出某些牺牲。”[12]这种“做出牺牲”,实际上是一种“迂回”的作战方式。从属阶级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很容易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持赞赏态度。《小说选刊》自2006年开始,在为读者做出“牺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2006年,选刊开始向西南边防哨所的战士定期赠送刊物并且推出了“零风险”订阅,承诺只要读者对刊物的内在品质不满意,年末凭邮局的原始订单和保存完好的12期刊物,就可无条件退款;2007年,《小说选刊》还推出有奖征订,并随刊附赠精美的藏书票和年历,第9、10、11期,为弥补为兄弟刊物发征订广告而损失的版面,还贴心地向读者赠送微型小说读本,并以充满感情的口吻告白:尽管“仅此增加的成本已超过20万元。但取之于读者,用之于读者,把钱花在大家的身上我们高兴并颇感欣慰”[13]。这一系列的举动自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这种情意浓浓的氛围中,选刊的价值导向意图也自然而然地为读者更好地接受。
综上所言,《小说选刊》2006年以来对“底层文学”的推举,不仅是利用“经济场”与“政治场”的审美趣味在“底层文学”上的重合,实现市场突围的过程,也是借助底层叙事的新锐势头,来确立刊物引领现实主义风潮的权威地位并试图重新建立起“文学场”的审美领导权的过程。尽管它在扶持、推动底层文学方面有种种不足,但其贴近时代、贴近人民的姿态以及对现实主义的重新呼唤在一定程度上使某些凌空高蹈的文学创作重新回到大地,纠正了写作和审美中出现的病象;同时,也客观上为文学增加了受众,显著地扩大了文学的社会影响。正如一位作者所说,“对走向滑坡的当代文学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这恐怕才是改版的最大意义。”[14]由此可见,《小说选刊》借助“底层叙事”对“经济场”与“政治场”的“妥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学场”的自救。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小说选刊》重新祭起现实主义的大旗,将现实观照的目光投向为人们所遗忘的底层固然不错,但它为“底层叙事”开出一味强调温情与善良的“苦难+希望”的药方,在矫枉过正的同时,是否陷入了另外一种伪现实主义的困境?另外,自2006年改版以来,《小说选刊》便将“通达好读,故事性强”作为一条重要的选稿标准,那么,“通达好读”的“底层故事”是否也暗示着对底层的一种隐性的消费?这些都是《小说选刊》在为一路攀升的订阅率欣喜不已的同时,需要深思的问题。
作者:赵婷婷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 上一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范文
- 下一篇:男式运动套装加工贸易单耗标准研究范文
精品推荐
- 1文学与文化论文
- 2文学专业毕业论文
- 3文学专业论文
- 4文学价值论文
- 5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 6文学作品分析论文
- 7文学作品影视化的利与弊
- 8文学作品论文
- 9文学作品鉴赏论文
- 10文学写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