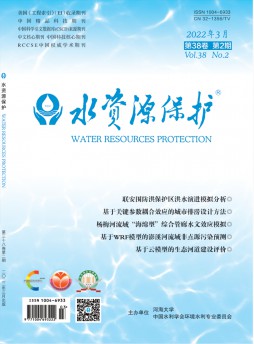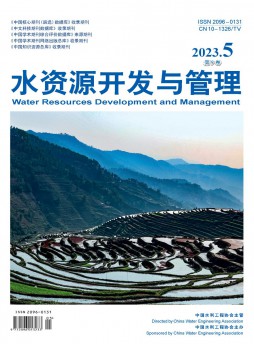水资源环境与乡村社会控制范文

一引言
汉中地区位于秦巴山区西段,“群山环抱,汉江合流。内为平壤,外则险。周以崇山峻岭,倚天插戟,断崖裂岫,蛇退猿愁”[1](p17)。清代隶属于汉中府,领一州(宁羌)八县(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沔县、略阳),后又增设留坝、定远以及佛坪三厅。水系以汉水为主干,汉水北岸水系,自西徂东,有沮水、褒水、文水、水、溢水、水、酉水与金水河等,纵贯于秦岭褶皱地带,支流的流向,多沿褶皱山峰的轴向东西贯注,或自西东流,或自东西汇,与秦岭南坡顺斜自北南流的河流形成方格水型,褒水及水之间,此种现象最为明显;汉江南岸各河流,或流经水成岩地层,或贯穿于火成岩块,对于河流的流向亦有不同的影响,在火成岩区,水系分布多为树枝状,在水成岩区,常以其构造为转移,没有方向可循,流向较为紊乱。[2](p42~44)降水分布的区域性差异亦十分明显。汉江以北年降水量以褒河为界,其东由南向北递增,变幅在900毫米~1000毫米;其西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800毫米~1000毫米。汉江以南和嘉陵江流域,年降水量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700毫米~1700毫米。由于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水量的季节变化明显。夏秋时期是雨季的集中暴发期,经常形成洪涝灾害。[3](p148~156,p103)这种水资源分布特点对汉中地区水利社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可以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从而使其成为我国著名的水利灌溉区。嘉庆朝的汉中知府严如曾言:“汉川周遭三百余里,渠田仅居其半,大渠三道,中渠十数道,小渠百余道,岁收稻常五六百万石,旱涝无所忧,古之有事中原者,常倚此为根本,屯数十万众,不事外求粮,其制渠之善,东南弗过也。[4](p2770)另一方面,降水多集中在7月~10月,且又因地形复杂,地势较高,常成为气旋徘徊停滞的区域,往往形成暴雨或者连阴雨,造成洪涝灾害,水利设施因而毁坏无定,要经常给予维修。城固县五门堰,“灌田四万八千余亩,然每当霪雨,必浩发,堤辄尽去,岁用柘施治,漂流如故”[5](p13)。洋县溢水、二郎等十二堰灌田六千余亩,但是“夏秋山水暴涨,每有冲决之患”,必须“随时修理,推沙筑石,视水之消长以时启闭,方可无患”。[6](p111~112)因此,汉中府的水利主要是灌溉与防洪问题,水利组织也多是灌溉与防洪并重。
关于汉中水利史研究学界已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水利工程技术、时空分布、农田水利的兴衰等方面,其研究的重点在水利而非水利社会。例如,周魁一以山河堰为中心对水利工程技术的分析;耿占军、桑亚戈对水利时空分布特征的考察;彭雨新、张建民等围绕着山区开发与水利发展进行的研究。近年来,张建民的系列水利史论文曾提出水利经营中的官督民修、绅衿作用以及水利冲突等问题。但是,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影响。因此,结合自然环境变化、社会经济制度的长期演变进行考察,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和很大的开拓空间。鉴于此,本文从社会生态史的视角,以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考察中心,利用量化统计的分析方法,围绕着几个典型水案,论证在自然与社会环境变迁的背景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适与整合关系,揭示清代汉中地域社会的变迁过程,希冀有助于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亦对生态环境史建设或有推动之意义。
二水资源环境变迁与水利兴衰
汉中府的水利灌溉以山河、五门、杨填三堰最为著名,其中最早的山河堰可上溯到汉代,相传于汉相国萧何时开始修筑,曹参最后完成。南宋乾道年间杨降《重修山河堰记》曰:“首访境内浸溉之原,其大者无如汉相曹公山河堰。”[7](卷六十《水利四》,p4)后历经各代,汉中水利尽管时兴时废,但总体上不断趋于完善,据笔者对清代该地区水利修建工程的统计分析,在具体记载修建过程的52项次中,新开筑的仅为10项,占19.2%,80.8%为修复原有水利设施。这一数字表明,至迟于明代汉中地区已经奠定了基本的水利格局。
清乾嘉以降,大规模的南方移民迁入,这些“南人”或者“楚人”继承了善于垦殖水田的传统,利用汉中地区优越的水系网络,就“溪河两岸”“筑堤障水”“以资灌溉”。至嘉庆、道光时期,不少原来没有农田水利的地方,由于这些移民的迁入逐渐发展起来。例如,略阳县,“县境无水利可言,近如娘娘坝、金池院坝、接宫厅等处有水田者,皆因川楚人民来此开垦,引溪灌亩或数亩、十数亩”[7](卷六十《水利四》,p37)。留坝厅,“留坝本无水利,近年以来,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两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开作水田。又垒石溪河中,导小渠以资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亩,小者数十亩不等,町畦相连,土人因地呼名”[8](卷四《土地志·风俗》,p5)。西乡县,“国初久被贼扰,遗民不能完赋。康熙、雍正年间,设招徕馆。南人至邑者,承赋领地,南人善垦稻田,故水利不及南郑、城固,而较胜于洋县”[9](卷八《民食》,p4)。因此,清代前期汉中地区的水利事业仍然获得进一步发展。
但是,与乾嘉以来移民的大规模开发相伴随的另一过程是,大量森林被毁,洪涝等自然灾害频发,山崩、泥石流、坍塌等山地灾害不断,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记:“南山老林弥望,乾嘉以还,深山穷谷开凿靡遗,每逢暴雨,水挟沙石而下,漂没人畜田庐,平地俨成泽国。”[7](卷一九九《祥异》,p1)道光《石泉县志》称:“近因山中开垦既遍,每当夏秋涨发之际,洪涛巨浪,甚于往日,下流壅塞,则上流泛滥,沿江居民沉灶产蛙,亦其常矣。”[10](卷一《地理志》,p2)道光十五年立石的《捐筑木马河堤碑》记,西乡县木马河,“曩时岸高河低,去城稍远,民不知有水患,近因林菁开垦,沙泥壅塞,水势亦漫衍无定,逼近城垣”[11](p266)。光绪二十九年立石的《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载有平利县坝河的变迁情况:“乾隆前,汝河口两岸石嘴造有铁锁(索)桥以济行人,名曰六郎桥……乾隆后,人烟日多,山地渐渐开垦,暴雨暴水,沙土将河填高,石嘴湮没,六郎桥化为乌有。”[12](p341)水利系统的完整性以及堰渠水利的灌溉效益受到严峻挑战。至道光时期,诸多堰渠水利的灌溉能力已严重萎缩。严如《三省边防备览》记:“汉中之乌龙江、水河各水,民循堰渠之规,田收灌溉之益,盖有利无害者。自数十年来,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各江河身渐次填高,其沙石往往灌入渠中,非冲坏渠堤,即雍塞渠口。”[9](p3)略阳县,“时值夏秋山涝,往往冲淤,不能收灌溉之利也”[7](卷六十《水利四》,p37);留坝厅,“夏秋山涨,田与渠尝并冲淤”[8](p5)。凤县,“两山相逼,中既水沟,民间安置水磨、水,所在多有。间或砌水堤拦水种田,而夏秋冲决,得不偿失。近年老林开垦之后,土石俱松,雨水稍多,浮沙下壅,反有水患而无水利。山地多淤平地十倍,农民旷地甚多”[13](卷一《地理志·水利》,p14)。
具体到某一堰渠或者某一次洪涝灾害,上述情况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杨填堰,“渠南地势低皆民田,渠北逼近山坡,坡日益开垦,堰口下里许曰洪沟,又七里许曰长岭沟,尤锯且深。每逢暴雨挟沙,由沟拥入渠”[7](卷六十《水利四》,p24)。嘉庆十五年夏季暴雨,河水屡涨,“堰淤百余丈,堰下二里许杨侯庙前渠道冲去一百一十余丈。渠截为两,河身夺渠北民地行,上下决口,在河中宝山上下,沙石壅塞,几与渠平,民坐失秋成”[14](卷二十《水利》,p48~50)。五门堰,“乾隆间河深下冲,渠岸渐高。春时农田用水,只在堰口移石砌坎,水即入渠,尚易为力。嘉庆六七年后,生齿繁多,山民斩木作柴,垦土种田,山濯土松。每逢暴雨,沙石俱下,横塞河身,冲压田禾,河失故道”[7](p22)。嘉庆十一二年的一次洪涝,“乃于百丈堰下,冲开东流夹槽,水从上流旁泄,竟致正河干涸,五门堰得水较难”[15](p253)。五渠堰,“从来蓄陂筑堰所以广水利之兴,而浚浍疏渠又所以除水涨之患。山内情形兴利与防患并重;平原沟壑处,今较创昔倍难。当年山地未开,沙泥罕溃;此日老林尽辟,土石迸流,偶值猛雨倾盆,便如高江下峡,一出山口,登时填起河身,四溢平郊,转瞬化为湖泽”[16](p13~14)。班公堰,光绪元年秋,“河水横发,冲崩老堰六十余丈”[7](卷六十《水利四》,p15)。
可见,清代汉中府堰渠水利的兴衰与该时期水资源环境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乾嘉以来水资源环境的渐趋恶化,汉中地区水利也出现相应变化,大量堰渠水利系统失去灌溉能力。三水利兴修与官民关系
清代,汉中府的水利修建主要有三种组织形式:官修、官督民修和民修。但是各自所占比重却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对有详细记载具体过程的52次修建活动予以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其52次修建过程中,官修18次,占34.6%;官督民修11次,占21.1%;民修14次,占26.9%;不能确定的9次,占17.4%。官督民修,看似官方参与水利维修过程,其实只不过是地方官的允诺批准而已,在具体修建过程中,仍由地方精英主持,民间具体实施。如洋县溢水堰,同治间,“知县李承玖督同首事、田户修筑如故”[17](卷四《水利志》,p11);光绪二十一年,“知县李嘉绩督同堰首廪生宋培、张敬铭、杨凤藻,附生白榆茂等,用石灰、桐油修筑完固”[7](卷六十《水利四》,p28)。显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是民间力量占主导地位。因此,如果将官督民修和民修两种方式合计,则民间共参与25次,所占比重达到48%。除去不能确定的9次,民修是汉中地区最为常见的堰渠水利修建的形式,民间比官方更广泛地参与了堰渠水利的修建,官方在堰渠水利修建中处于次要的地位。从纵向看,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就整个清代而言,民间的参与越来越居主导地位,官方势力逐渐减弱(见图1)。
从图1中很容易看出整个清代汉中地区水利修建的变迁情况。乾嘉以来,民修水利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修水利呈下降趋势,民修水利已成为主要形式,水利的民间化日益显现。
水利组织民间化趋势的另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政府依靠地方精英阶层对水资源实行间接化的管理。关于水资源的管理涉及到堰渠开凿与修浚资金的来源、工程组织、渠规制定、渠务管理与监督等一系列问题。这里我们以泉水堰、五门堰、杨填堰等一系列典型水案为例进行分析。
泉水堰位于沔县境内,以龙洞泉水为水源。咸丰九年《处理泉水堰纠纷碑》记载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小中坝泉水堰,自龙门发源,系拾贰家军户之私堰,沿河两岸,支流汛泉,总归此堰,外人不得开地作田,阻截上流。由泉远水微,田亩粮重,旱地粮轻,只许十二家军户轮流支灌,自有明如是,无敢违者。”[18](p293)可见,泉水堰始建于明代,最早是12家军户修建的私堰。该碑还详细记载了道光十一年至咸丰九年的5次水利冲突,为考察水资源管理的运作情况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兹录如下:
道光十一年,有客民陈正秀开地作田,违例霸水,被堰长投约,处明具结,永不得拦截堰水。十四年,有阻拦堰水,亦具永结。又十五年,张文兴、李普、王修德等,估截此堰上流之水,被堰长具禀在案,蒙县主李断令,仍照旧例,立碑为记,外人不得紊乱。及到回家,伊等藐违公断,抗不立碑。彼时俱言堂断可凭,即不立碑,量亦无妨,伊等竟未立碑。至道光二十年,突出陈正秀之胞弟陈正章违例开端,胆将堰源拦阻涸断,堰长查明,赴城具禀,陈正章唾托王大德诱诓拦回,竟将堰长刁控。嗣蒙票唤,陈正章自知理屈,请同黄沙驿、小中坝两牌乡约说合,亦具永结,永不敢拦截堰水。二十一年,陈正秀又使其子陈有刚、陈佘娃、陈周儿,拦截此堰上流之水,堰长往查理阻,伊等恃恶逞刁,反将堰长按于水中,淹浸几毖。陈正秀自觉理屈,希图逃罪,径从小路进城捏控,蒙县主朱朗鉴批示:明系窃放堰水,先发制人,姑候唤讯究质,如虚倍惩不恕等语。随后堰长亦有具禀。陈正秀睹视批词,知难对质,仰托亲友,请仝乡约,再四与堰长、田户赔罪,跪求饶免,堰长、田户亦从宽姑恕。迄今二十余年,无复有敢截渠源者。不料今岁七月十六日,有张文兴之子张武刚,陈正秀之孙陈二狗,李普之侄李茂春等,复恃强违例,将此堰上流截拦,勺水不下。堰长、田户情急往查,拿获伊等护戽、水车等物,即欲具禀恳究,伊等自觉情罪难容,请托武举关雄望邀约牌内绅士、田户说合,伊等情愿认立石碑,以志规例;演戏三日,晓众警顽。自此之后,勺水不敢入于旱田。[18](p293)
从该资料可见,由于水资源环境变化,晚清时期泉水堰水利冲突不断,尤其是矛盾的最终解决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大多经由乡绅、乡约、堰长、首事等精英阶层的参与才得以解决。道光十一年,“被堰长投约,处明具结,永不得拦截堰水”。道光二十年的冲突,“请同黄沙驿、小中坝两牌乡约说合,亦具永结”。道光二十一年的矛盾“仰托亲友,请仝乡约,再四与堰长、田户赔罪,跪求饶免”才最终解决。咸丰九年的冲突,“请托武举关雄望邀约牌内绅士、田户说合”。堰长和乡约成为解决水利冲突的关键人物,在水资源管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官府具有最后的裁决权,但从泉水堰水利冲突的解决过程看,双方当事人往往会尽量在正式的诉讼判决前由堰长、乡约予以协调解决。即便是由官府判决,也要考虑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规约。如道光十五年的冲突,知县判定,“仍照旧例”,而所谓“旧例”无非是“外人不得开地作田,阻截上流。由泉远水微,田亩粮重,旱地粮轻,只许十二家军户轮流支灌”这一自明代一直流传下来的用水习惯。光绪《沔县志》的记载也说明此点,“每见乡民聚谈,动称军务事大,堰务事大,某官懂水利,某官不懂水利。推其所谓懂水利者,则水利词讼但照旧章断结,所谓不懂水利者,则不照旧章断结而已”[19](卷一《地理志》,p30)。
与乡绅、乡约、堰长、首事等这些基层社会精英在水利社会中的地位日益显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府的权威却日益受到基层社会的挑战,这一点晚清时期更为突出。城固县五门堰,光绪三年,油浮、水车二湃,“偶遭奇旱,西高渠虑难得水,迭次控争,官经数任,谩讼不休”,到光绪四年三月,“定远厅余丞,驰赴该处,会同前署县徐令,勘明讯断”,仅一个月,四月十二日,西高渠绅粮杨春华“意欲独擅其利”,“率人挖毁所修渠底平石”,最后官府不得已“选派练兵营弁勇”,“驻堰弹压”。[20](p327~328)杨填堰,光绪二十四年春,“西营村廪生张成章贿窜百丈堰首事刘永定,与村民张玉顺、张畏
三、张贵发等以旱地作田,于洪沟桥搭木飞漕,接去五洞外若干济急之水”。十月,“吕家村吕璜等偷砍西流河护堰之柳,私捏造具;狡骗河西拦水坝地址,凶阻工人,不准拣石修堰”,由此而起的诉讼先后至县、府、道依然未能解决。二十五年四月,借插秧之时,张成章等又“预备搭漕灌溉”,争诉又起。五月十八日,王县令“带差亲赴西营村拆毁飞槽”,张玉顺等竟“纠众殴官”。[21](p357~358)尽管最终在陕安道道台恩开的支持下矛盾得以解决,但是这一系列反复过程,尤其是殴打县令的事件,说明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有逐渐削弱的趋势。政府官员由最初的积极参与水利兴修到后来的督导与协调,最后竟然被村民殴打,这一前后变化是否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但是,这种民间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官方的毫无作为。如前所言,官民力量的消长是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官方力量的退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康熙及雍正时期水利的兴修基本上仍由知县等地方官员来主持。乾嘉以降,修浚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才逐渐转向以乡绅与其他地方精英为代表的基层社会组织,以知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修浚过程中的身份是由主导者转变为督导者,但不是完全退出。尤其是在汉中地区水环境日益恶化、水资源分配复杂、水利冲突增加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固有的分散性、保守性弊病,必须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进行调控与克服。知府严如□请恢复水利通判以期解决相关问题的建议就颇能说明问题:
缘近日以来,老林开垦,土石松浮,每逢夏秋霖雨过多,遇有水涨,溪河拥沙堆石而行,动将堰身冲塌,渠口堆塞,必乘冬春雇募人夫,修砌挑挖,使水之时,方能无误。工费日加繁重,需用银钱,虽按地均摊,民间各举首事收支,而派发人夫必须官为督催方用。命其各县所管堰渠与他县不相交涉者,地方官即自行督办尚易,经理内如南褒之山河大堰、第三堰、流珠等七渠及城洋之杨填堰,均一渠浇灌两县田亩,一应修堤、挖沙、拾拦河、筑洞口各工,或上游恃其易于得水,不肯照例行夫,或尾坝诿以难于得水,不肯踊跃从事。至使水之时,或将洞口尺寸私行挖宽,或于封洞日期暗行盗启,人户既众,有属两邑关查移讯动需时日,以至挑修不能赶紧,栽时或至误期,若委员督办,终非专管之官,事多掣肘,或届署事不能久留,更易生手,辄至茫无头绪,小民辄起争端,此士庶恳请设官经理之实情也。[17](卷四《水利志》,p5)
官府的鼓励和督导有时也确实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西乡县金洋堰,乾隆十六年夏,“暴雨丕作,冲崩坍塌,堰之故址,杳乎不可复识”,尽管“董其事者”“率众修葺”,但“无如呜(乌)合之力难齐,势将日就废坏”,幸逢“刘老父母(知县刘灼)留意民瘼,目击心伤,即日亲临河干,庀材鸠工,督众共举??其惰者,量力扑责,用警殆玩;而勤于用力者,即劳之酒食,赏以青蚨”,于是,“一倡百和,众力踊跃,淤者以浚,废者以兴,不数日间,而堰工告成矣”。[22](p214)城固县五门堰,嘉庆八年后,河水屡发,屡修屡冲,因修渠引起的水利争诉不断,堰渠水利几度荒废。至十三年,“四里强将堰堤裂段分修,彼此争胜加高,激水奋溢,五洞与官渠堤岸,屡修屡冲,工程愈重”,一直到嘉庆二十
二、二十
三、二十四年,县令亲履堰所,“开导愚氓,劝令四里合工”,知府“按临勘验,劝谕谆谆,曲尽其法”,才于二十五年“竭力奉行,不欲虚耗民财。越夏至秋,堰堤稳固,五洞渠岸俱无恙”。[15](p253)而且官府有时也会从长计议,进行筹划。西乡县五渠堰“乾隆以后,山荒开垦,水故为患??道光六年五月,山水下涨??知县传绅耆居民捐廉、倡助,按亩役夫,五渠同修”,并且“令各渠上密栽桑树……将北山封禁,以绝后患。各山地主情愿遵论,不再开挖,各栽桐漆等树”。[7](卷六十《水利四》,p24)民间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主动请求地方政府的协助或保护。杨填堰,嘉庆十五六年,“山水频涨,杨填堰旧渠平为河身,两邑士民公请于知府严如,(严)以洋邑贡生蒙兰生总理修复,又城洋武生李调元、张文炳、高鸿业等共襄其事,买河东岸地一十四亩,将渠身改进”[7](卷六十《水利四》,p33)。杨公堰,嘉庆十五年,“居民李凤发倡,首呈请知县杨大坦开田筑堰,年工成”[7](卷六十《水利四》,p13)。
可见,与前期主动参与修建有所不同,政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被动的介入,但这未必就意味着官府力量完全退出。应该说,这其中既存在着官方与民间社会力量的此消彼长,同时也存在着彼此目标的一致性和彼此利益的协调,尤其是在汉中地区社会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这种协调性共同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当然,从长时段看,清以降,政府控制更为间接化,汉中水利组织日益呈现民间化趋势。前述水利修建过程中,官府身份角色的转变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国家权力控制基层社会方式的转变。
四官民力量消长的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水利组织的民间化趋向,官民力量的这种消长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地方官府缺乏必要的财政支配权与充足的财力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水资源环境的恶化更使其雪上加霜。
从一条鞭法发展到完全的“摊丁入地”是明清时期赋役制度改革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亦是清代社会变迁的财政经济根源。当然,这一转变过程,是一种历史的与地域的发展,各时各地的方法都不完全一样。据笔者所见资料,汉中地区最早实行“丁随粮办”的县份是城固县,该县于崇祯八年“丁随粮行”;南郑、褒城于顺治十三年“丁随粮行”。[23](卷三《纪丁随地起》,p119)洋县最晚不会迟于明代末年,知县邹溶记载:“粮赋出于田地,地丁银出于生齿,从古然矣。洋乃丁随粮起,不论秋粮夏豆,每斗科丁银一钱。盖不知始自何年,父老相传,大率明末兵灾之后,丁额太缺,彼时不能邀减,故就粮均科不过一时权宜,岂意因循成例,而粮内又有荒绝苦累益甚幸。”[17](卷二《风俗》,p4)
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颁布诏书“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到雍正五年全面实行“摊丁入地”。汉中府各地基本上都先后实行了这一政策。摊丁入地作为一条鞭法的继续与发展,其顺利的推行具有很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一条鞭法所开始的税收定额化、税则简单化、税种单一化的改革方向,都在摊丁入地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和确认,经过摊丁入地的改革,各级政府的正项赋税归并为形式上单一的土地税”,“为形成更为集权化的财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24](p117)财政收支纳入规范化的管理,杜绝、减少了地方上的滥收、滥征。沔县,“自雍正五年均丁于粮,而民间不复知有徭役”[19](卷二《赋役志》,p17)。尤其是地方钱粮收支进行集中管理与审核,除去赋役全书定例支给俸工等项常规性开支外,地方上的一切额外开支,均需先题请户部批准,方得动帑。这样一种集权化的财政管理体制,其作用一方面有利于加强清王朝集权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则对于地方上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以及一些大规模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修,往往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或者财力不足的问题。光绪《白河县志》载:“白邑非无渠堰,但堙塞日久,水利尽废,公帑支绌,浚治为难,每岁申详上宪,仅存具文,是一饩羊类也。”[25](卷三《渠堰》,p6)尤其是乾嘉以来汉中地区的水环境日益恶化,洪涝、泥石流等一些极具破坏力的突发性灾害频发,这种集权化的财政管理体制必将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现实。因此,州、县政府在此情况下,也只能寻找其他途径。由州县官自己捐款,或者说服乡绅和富人集资。例如,山河大堰之正身柳边堰,“嘉庆七年,布政使朱勋任陕安道,捐廉一千五百余两,修筑石堤五十五丈,工称巩固。至十五年夏秋水涨,于石堤下将旧堤身冲决成河,两邑士民请于陕安道余正焕、知府严如,议就石堤上下加筑土堤七十九丈……委官同两邑绅士开凿”[14](卷二十《水利》,p12~13)。西乡县五渠堰,道光六年,“山水下涨,营署民房又遭冲坏??知县张廷槐传绅耆居民,捐廉倡助,按亩役夫,五渠同修”[26](p13)。
财权管理集权化的另一个集中体现是起运、存留额的比率变化。根据陈支平教授研究,明代田赋起运额和存留额的比率,虽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的看来,地方财政的存留数量在整个田赋总收入中,占有相当的比重。[27](p89~106)清代,在制度原则上沿袭了明代的起运、存留方式,但是在起运、存留的分成比例上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大幅度地裁减地方财政的存留,增加中央政府的起运数额。笔者谨根据所掌握的文献资料选择南郑、褒城等五县,就汉中府清代起运、存留数变动情况列简表1,以反映其中的大体趋势。
根据表1可知整个清代汉中五县起运、存留比率的变动情况,尽管各地不同时期存在波动,但总体上看,各地起运比例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地方留存的数量越来越少。这一变动所产生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各地方官甚至连最基本的行政费用都难于维持,更别说兴修、维护水利这样的公共设施,地方政府所担负的公共职能势必会削弱。如留坝厅,嘉庆时期地丁钱粮共计不足300两,而仅留坝同知的薪俸与养廉银就达830余两,如此大幅度的入不敷出,那里还有修建水利的资金。[14](卷十二《食货》,p1)与此同时,汉中地区的水资源环境又不断恶化,水利修建的频度增多,杨填堰、五门堰、五渠堰、土门堰等堰渠工程因水环境的恶化不得不频繁维修,成本逐年增加,所需资金数量也越来越大。例如,城固县五门堰,“乾隆间河深下冲,渠岸渐高。春时农田用水,只在堰口移石砌坎,水即入渠,尚易为力。嘉庆六七年后,生齿繁多,山民斩木作柴,垦土种田,山濯土松。每逢暴雨,沙石俱下,横塞河身,冲压田禾,河失故道。用水之时,不得不截高坎、钉木圈,垒石为墙,以防水冲。然大水之内决洞梁,外田禾,浸村庄,愈冲愈宽。五门堰截坎直至三里之遥,每亩派钱五六百文,较雍正时,渠费不啻倍蓰,农民身受其病。而无赖首事以为利贿通县役,逐加用费,小民窘苦,结诉连年”[7](卷六十《水利四》,p22)。嘉庆二十五年《五门堰创置田地暨合工碑记》亦载,“每岁春间,不过按亩起夫,捡石平砌??铲取草笆,以为漏水,即敷灌溉,使水人民并不劳民伤财”,至嘉庆八年后,“河水屡发,冲淌地亩,淤成沙坝,河滩无石可取”,不得已只能“按亩派钱,买石修堰”。[15](p255)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光绪年间,而且日趋严重,“每当秋夏之交,洪涛暴涨,堰之堤防,斗山直渠坎,皆不可保,岁屡歉……然而工日繁,田日简,费尤日益”[28](p325)。面对如此情景,地方政府本应该加大对水利的投入,增加修渠资金,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配数量日益萎缩,财力匮乏,只能越来越倚重于民间社会了。
可见,明清以来,官修水利的衰落,民修水利的勃兴,官民力量的这种消长与明清以来一系列赋役改革所确定的集权化的财政管理体制直接相关,其集权化的管理体制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所担负的传统的社会公共职能,以前由地方官府主持、出资的公共事务由于资金的匮乏不得不拱手让出;在民间社会,地方精英则担负起这一责任,水利修浚资金也向民间筹集方式转移,水利兴修日益向民间社会转移成为发展的大趋势。
综上所述,清代汉中地区的乡村水利社会不断变迁,伴随着乾嘉以来的移民大开发,堰渠水利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开发的不断深入,民间行为囿于小团体利益而缺乏整体性、全局性考虑的弊病又日趋凸现,汉中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水利社会亦发生明显变迁。这一变迁不仅包括诸如水利设施兴废、水利冲突强弱等表面现象,还涵盖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整合关系。在自然、社会环境变迁的背景下,汉中水利社会日益显现出社会控制权的下移。由于“正规政府能否担负这些责任的程度要视其行政能力的强度而定”[29](p215),因此随着有清以来财政赋役制度的变革,政府的支配力量日渐削弱,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国家行为越趋间接化,地方政府在诸多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已不及基层社会。但如果说乾嘉以后汉中地区的水利事务完全脱离官方的社会管理,也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乾嘉以降,在水资源环境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官府力量似乎又显得重要起来。这看似十分矛盾,但实际上反映的是历史的现实。这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的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予教条性概括,必须纳入到具体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去考察。参考文献:
[1]刘于义修,沈青崖纂.陕西通志:卷七,疆域二[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R].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
[3]聂树人.陕西自然地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杨起超主编.陕西汉中地理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严如□.汉中修渠说[A].贺长龄,魏源.清经世文编:卷一一四,工政二○[Z].北京:中华书局,1992.
[5]重修陕西城固县五门堰[A].周馥纂.治水述要:卷四[M].1922年刻本.
[6]卢坤.秦疆治略[M].道光年间刻本.
[7]杨虎城,邵力子修.宋伯鲁,吴廷锡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六十,水利四[Z].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8]贺仲瑊修,蒋湘南纂.留坝厅志[Z].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9]严如□.三省边防备览[M].清道光年间刻本.
[10]舒钧纂修.石泉县志[Z].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11]胡延瑞.捐筑木马河堤碑(道光十五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12]黄岑楼,丁震.创设坝河垭公渡记暨公议船规碑(光绪二十九年立石)[A].张沛编著.安康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13]朱子春修,段澍霖纂.凤县志[Z].光绪十八年刻本.
[14]严如□修,郑炳然等纂.汉南续修郡志[Z].嘉庆十九年刻本.
[15]李时中.五门堰创置田地暨合工碑记(嘉庆二十五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16]张廷槐.重修五渠碑记[A].张廷槐纂修.西乡县志[Z].光绪八年刻本.
[17]张鹏翼纂修.洋县志[Z].民国二十六年石印本.
[18]徐步云.处理泉水堰纠纷碑(咸丰九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19]孙铭钟,罗桂铭修.彭龄纂.沔县志[Z].光绪九年刻本.
[20]修渠定式告示碑(光绪五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21]处理杨填堰水利纠纷碑(光绪二十五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22]邑侯刘父母重修金洋堰颂德碑(乾隆十七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23]王庆云.石渠余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24]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制的形成[J].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一辑[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25]严一青纂修.白河县志[Z].嘉庆六年刻本.
[26]张廷槐纂修.西乡县志[Z].光绪八年刻本.
[27]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28]周曜东.五门堰复查田亩碑(光绪元年立石)[A].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Z].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29]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M].王旭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注:文中图表和个别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