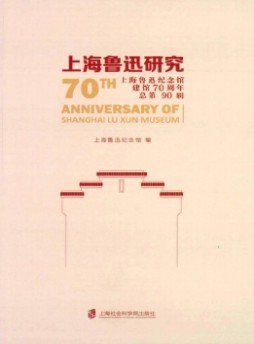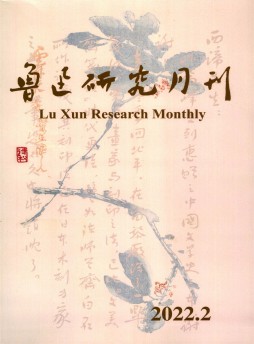鲁迅作品中母性受难的意义范文
时间:2022-10-08 03:04:18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三期
鲁迅在杂文《小杂感》中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母亲形象多次出现在鲁迅作品中,除了《社戏》、《故乡》和《在酒楼上》中的慈母,像《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孤独者》中的祖母,《颓败线的颤动》中的母亲,尤其是《药》中的两位母亲,以及《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一些不识字的丧夫者、孤独者、迷信者,或者“粗笨女人”。她们有的无名,有的无名无姓,是令读者同情的苦难母亲。不过,“同情”可能恰恰暴露了读者“革命/启蒙”视野下居高临下的立场,以及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思维方式,这种“现代(进步)的”或“人道主义式的”解读忽略了本源层面上的“母性”存在,遮蔽了母性受难的困境及其批判性和救赎性。这在研究界对《药》和《祝福》的解读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一、被遗忘的“亲子之爱”
以往对《药》的主题理解大致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从揭示革命者的悲哀、革命失败的原因,到批判群众愚昧、寻求现实改造的变化,在这两种实质相似的视野下,小说中的另一条主线———“亲子之爱”往往被遗忘和遮蔽了。无论是“革命”还是“启蒙”的解读都聚焦于把“人血馒头”当作“药”这一“封建迷信”。所以这里的首要问题是怎么看“人血馒头”。当读者看到“用人血馒头治病”(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已提及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犯人的血舐),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和“愚昧”,何况这血又来自就义的革命者夏瑜,那么“愚昧”后面又要加上“麻木”和“残忍”了。事实上,用鲜血治病在中国的民间就像“吃什么补什么”一样,没有科学依据,当然是一种“迷信”,但鲁迅对这一类民间“迷信”并非简单否定了事。在1905年发表的《破恶声论》中,鲁迅把当时的改良人士视为“迷信”的种种宗教、民间信仰、神话和神物等等,都看做是“人”的一种精神性(尤其是古民的“白心”和“神思”等想象力)的产物,是“不安物质之生活”的“人”的“形上需求”。
如有论者指出的,“鲁迅既不是在‘近世文明’的立场上批判民间信仰,也不是作为传统的维护者将民间信仰实体化、绝对化,他是在反思‘近世文明’的立场上看待民间宗教与迷信的,挖掘其精神气质以作为反思‘近世文明’的思想资源”。在鲁迅看来,关键问题不在于“迷信”的对与错,而在于信者的态度是否真诚(是否真“信”)。像祥林嫂、阿Q、华老栓、华大妈、夏瑜的母亲这样的底层百姓,他们一辈子生活在“迷信”的传统中,没有机会领受一种“现代”的知识和观念,不会意识到自己的“迷信”。但与那些追逐新潮价值、内心不信却又信誓旦旦的“浇季士夫”相比,他们起码是真的在“信”。迷信的世界就是他们的生活世界。而那些动辄指斥民众的宗教信仰为“迷信”,而自己却不知“正信”为何的人(多为受过教育的知识人)反而是“伪士”。鲁迅最后的结论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早期鲁迅的这一宗教和迷信观到后来并没有根本变化。这提醒我们不要囿于“启蒙”或“革命”视野,在科学(进步、觉醒)∕迷信(麻木、愚昧)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去理解《药》。二元对立化理解的表现之一就是忽略了《药》中的“血”具有双重性,即“革命者之血”和父亲母亲与儿子间的“血缘之血”。我们往往只注目于作为“药”的“革命者之血”(“人血馒头”),注目于革命者之血和不知革命为何物的民众之间的错位———“血”作为(启蒙之)“药”最终失效了,是革命者也是群众的悲哀,而忽略了,这“血”也是真实的、身体及情感上的“血”———血缘之“血”。它是革命者夏瑜的身体之血,也是痨病患者华小栓的身体之血(痨病的症状之一是咯血),在血缘的意义上,它关联起两个母亲、两个儿子,体现的是“亲子之爱”,即父爱和母爱(在小说的结尾,母爱又被特别凸显)。
“亲子之爱”说是朱自清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来的。他认为“亲子之爱”是《药》的正题旨,革命者的悲哀是小说的副题旨。后来我们先是将正、副颠倒,再后来就不再提“亲子之爱”了。从内容看,“亲子之爱”在小说中是贯穿性的存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写老栓去刑场拿药。无论是老栓去的路上“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的感受,还是拿到“药”之后,“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都以老栓的行动和感受为中心。叙述人对老栓没有讽刺。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一是华老栓(和华大妈)并不知道被处决的是一位革命者(也就是说,以夏瑜的“血”做药与他的革命者身份没有关系);二是在叙述人的眼中,老栓与那些“古怪的”、“鬼似的”、“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像被捏着脖子的鸭”一样的看客(他们也出现在阿Q的行刑现场)有着明显不同(这些看客恰恰是通过华老栓的视角呈现的)。第二部分写小栓吃药。“他(小栓)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上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在这些描述中可以切实感受到父爱母爱的存在。这是一个充满关怀的家庭场景,没有讽刺性的话语出现。
小说第三部分的主角无疑是康大叔。他一出场就可看出与华家三口的不同(也与茶馆中其他人不同)。康大叔对小栓漫不经心的“一瞥”(茶馆内其他人也对小栓的咳嗽不以为意)与华大妈对“痨病”的敏感和对儿子的担忧形成潜在的对照。从这里可以看到,同是群众,老栓一家与康大叔不同,与牢头红眼睛阿义不同,与那些刑场的看客不同,也与茶馆里的顾客(驼背、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不同。后面这些“群众”也许可以称之为“愚昧”的。不过,小说的目的并不止于表现和批判“愚昧”。小说的第四部分最容易引起歧义。立足革命和启蒙视野的解读都被那一圈花环和那一只乌鸦所吸引,而忘了两个悲哀的母亲。如果置诸于“启蒙”和“革命”的逻辑,那么花环和乌鸦就一定有象征的深意:“花环”意谓革命烈士没有被所有的人遗忘,还有人纪念他们(因此革命仍然有希望);而乌鸦,大多数人认为它象征着“革命”。乌鸦飞去则否定了夏大妈的“显灵说”,说明母亲不理解儿子,不理解革命(当然也就不理解“花环”的意义)。上述理解将小说当做象征和寓言来读(所谓“华夏”的命运),而忽略了小说的现实基础,因此就会出现有论者指出的问题,即“过于关注作品中的象征符号,由于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和象征符号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对作品象征内涵的把握很有可能成为研究者对象征符号的个人演绎”[7]。既然花环是作者鲁迅自谓“不恤用了曲笔”“平添”上去的,它的涵义就未必有我们所说的那么确定。即使它象征着“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不仅仅指向“革命”,也指向对孤苦无援的夏大妈的安慰(同时它又让另一个母亲华大妈感到“不足和空虚”)。上述理解除了有将象征含义过于“落实”之嫌外,还隐含着将革命(启蒙)与“亲子之爱”对立的趋势,认为母爱的蒙昧、自私对于革命者和革命是一种束缚和负担。这无疑是受我们的“启蒙/革命”视野所限。其实在中国民间,乌鸦既是只不吉利的鸟,也是一只“神鸟”,一只“孝鸟”。在鲁迅故乡绍兴的目连戏中(它深深地影响了鲁迅),它被称作“慈乌”。日本研究者丸尾常喜就特别注意到在绍兴目连戏《目连救母》中“乌鸦反哺”的情节。他把乌鸦看做“虽然背负着自身的不孝与母亲的悲哀,但仍坚韧地走向前方的‘不孝的孝子’们的革命意志的象征”,所以小说写的是“革命者的救民意志与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悲剧性隔绝”。
二、母性的批判
径奔“血”的象征意义而去,而有意无意忽略了更基本的、血缘之“血”的存在,使得“亲子之爱”要么被遗忘和遮蔽,要么被视为“蒙昧之爱”。那么这两种“血”,或者说,“革命、启蒙”与“亲子之爱(迷信)”是什么关系?无论是朱自清的“正负题旨说”还是丸尾常喜的“革命者的救民意志与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隔绝”说,抑或是后来的“革命/启蒙”立场下对民众(包括两个母亲)之愚昧的批判性解读,都没有去追问这一问题。其实,正是小说第四部分中两个母亲的表现(稍后会论述),让两种“意志”、两种主题、两个价值世界产生了内在的关联。这里仅仅用“亲子之爱”或者“母爱”不足以概括两个母亲。因为她们的存在与其说是体现了某种母爱,不如说是凸显了“母爱”在现实世界被剥夺的命运。但是,即使被剥夺了做母亲的权力,那母性的声音却仍然绵绵不绝。这是一种本能,被动甚至愚昧,却又是执着、包容的,这是处于受难中的“母性”。正是它,让《祝福》中的“我”———一个现代知识者不安。与《药》中两个沉默寡言的母亲不同,《祝福》中的母亲祥林嫂以一连串的提问和反复“念叨”的方式令人侧目。祥林嫂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被鲁镇的人们最终“弃在尘芥堆中的”的最底层的寡妇,却出于信任,向“我”———一个“出门在外见识多”的读书人一连提出了三个问题:人死后有没有魂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如李欧梵所指出的,“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虽然是从迷信出发的,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而且和‘我’的模棱的、空洞的回答形成惊人的对比,因为作为知识者的‘我’,本是更有可能去思索生死的意义的。”
这三个问题可谓是“迷信”对“启蒙”的反问,它超出“科学”或者“启蒙/革命”话语所能够把握、阐释的范畴,也是人道主义式的同情所不能回答的。不过“祥林嫂之问”是否就如研究者们所说,是关乎“生死意义之问”或者“信仰之问”,从中可看出祥林嫂的“觉悟”有多高,或者信仰有多深?从母性的角度看,祥林嫂更多是作为一个(丧子、丧偶的)母亲和妻子在提问。这是她的切身之问(死后与家人能否见面),是忧心的母性在寻求安慰,所以祥林嫂是既希望其有,那样与儿子就可以见面,又害怕其有,那样身体会被锯成两半。不过从她急切的语气可推测她希望其有。在这里母爱压倒了恐惧。而“我”的落荒而逃应该理解为自以为掌握着这个世界的阐释权的启蒙的挫败,可见“我”并非一个坚定的启蒙者和无神论者,否则就应该直接给予否定的回答了。他没有办法拯救像祥林嫂这样最底层的无助者,甚至连最后(也是最基本)的安慰都不能给予。启蒙者在母性逼视的目光面前,在母性的受难面前无能为力,这是让“我”长久处于“不安”当中的根本原因吧。
也正因为这种“不安”驱使‘我’去追述祥林嫂的生平。在其中,祥林嫂对儿子阿毛之死的“念叨”一再出现,驱之不去,纠缠着鲁镇的人们,以及叙述者和读者。“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祥林嫂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诉说儿子被狼吃掉的经过,最终让鲁镇的人们烦厌得头痛。祥林嫂的“念叨”首先是一个母亲对死于狼口的儿子的哀悼;其次,一再的重复表明她想(在自己和鲁镇人面前)继续维持作为“母亲(而非妻子)”的身份;第三,它也类似于宗教徒的“忏悔”和“告解”。不同的是,祥林嫂倾诉的对象不是上帝、神甫或菩萨之类,而是鲁镇的人们。她倾诉的方式不是私密,而是公开的,她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公开的告解方式寻求解脱。她就像自觉“有罪”的苦役犯,但她的“罪感”不是来源于信仰,而是出自母性的天性。和捐门槛一样,一再的重复(告解)也是祥林嫂的赎罪方式。可是鲁镇没有一个类似于神甫的告解对象,也不存在一个让人在罪中复活的上帝。他们先是厌烦、唾弃了她的告解,又否定了她的捐门槛的赎罪方式。祥林嫂的无法求得救赎,鉴照出“我”所代表的启蒙理性的缺失,鲁四老爷所代表的儒家理学和家族制度的缺失,以及鲁镇的“祝福”仪式中神性的缺失。鲁镇的人们相信鬼神,注重家族祭祀的仪式,却缺失最关键的实质———神性和救赎、爱与怜悯。先后失去丈夫和儿子的孤苦无依的母亲,在“祝福”的时刻被鲁镇整个地排斥在外,在惶恐和绝望中死去,这是母性的受难,也是“人性”的受难。正是借助母性的受难,小说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和反讽———这大概是鲁迅对中国文化最深层的揭示和批判了———中国的人间和地狱,皆不包容受苦者、绝望者,不能让丧失的母性得到最终安慰。因此小说的标题“祝福”只能从反讽的意义上去理解。更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一母性的受难图中,“我”与鲁四老爷(及鲁镇的人们)扮演的角色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异。而当读者亦认为祥林嫂“无知/愚昧”,不耐烦甚至取笑祥林嫂的一再“唠叨”时,我们也与鲁镇的人们一样,在祥林嫂的母性的“绝望”中扮演了相似的角色;或者当我们仅仅把祥林嫂视为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所谓“夫权、族权、神权、政权”下的“牺牲品”,并予以同情时,我们也仍然遮蔽了祥林嫂之母性“受难”的尖锐批判意义。
三、母性的救赎
丸尾常喜说:“为了万人之生而宁可一人赴死的夏瑜的意志,与为了小栓的生命而罄其所有的老栓的意志,本来可以作为共通的东西紧密地结合起来。可是,在这个舞台上,二者却决不相触,各自散发着孤独的光,一起为某种强暴之力所扼杀。”可是因为母性的存在,隔绝的二者有了交集。而《祝福》中母性的受难在揭示了“人吃人的世界”的真相———一个缺乏爱、怜悯与救赎的世界的同时,也把这个世界撕开了一个裂口,人吃人的循环因此有被打破的可能。这可以说,母性的受难既是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又是对它的救赎。因为在苦难的深处,“人性”总会与“神性”相通。不止一个研究者指出《药》中夏瑜牺牲与耶稣受难之间的关联:“耶稣也好,夏瑜也好,他们首先觉醒,甘愿牺牲,人格高尚,却无法避免自身的牺牲也被误解的悲剧命运”。。也有人注目其差异性,认为夏瑜作为革命者的牺牲中看不到神性。耶稣之血救赎了众人,成为救赎众生的灵药,而夏瑜的血则没有。《药》中有一个“人子受难”的模式,但与《圣经》中的耶稣受难有本质区别:“夏瑜的牺牲没有从任何意义上得到认可。作为人子一代的鲁迅对自己在中国进行启蒙革命的意义产生了彻底的质疑,并伴随着深深的悲凉”。以上都是从夏瑜、耶稣牺牲与受难的结果而论。李欧梵则指出,“在这篇小说的象征性框架中,怜悯的举动给牺牲的意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在受到肉体虐待时仍然给予怜悯,这种举动显然受到耶稣基督的启发……然而,他与耶稣不同,他没有上帝作为更高的权威,最终的意义问题不可能得自任何超验的来源。这便是鲁迅人道主义的最后悲剧。”
确实,如果只着眼于夏瑜与耶稣的牺牲,那么二者之间的差异明显:两人流血的目的不同,结果不同,尤其是夏瑜的牺牲中没有救赎的希望(而耶稣经由牺牲后的“复活”成全了救赎)。这是“人”与“神”、“人性”与“神性”的区别。但是当我们的目光不受“启蒙/革命”或“人道主义”框架的约束时,反而可能发现母性受难与耶稣受难之间的内在相通。在《药》中,它集中地体现在小说的第四部分。这部分首先是通过华大妈的视野呈现,花环出现时两个母亲的视野开始融合。如果一开始两个母亲还是被一条区分死者身份的小路隔开的话,那么华大妈出于关心,跨过小路安慰夏大妈,就意味着她们之间因为儿子之死而打破界限。许多的工夫过去了;上坟的人渐渐增多,几个老的小的,在土坟间出没。华大妈不知怎的,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便想到要走;一面劝着说,“我们还是回去罢。”那老女人叹一口气,无精打采的收起饭菜;又迟疑了一刻,终于慢慢地走了。嘴里自言自语的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如作者自谓,《药》的这个结尾有些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和“鬼气”。
如前所述,不管花环和乌鸦是不是象征革命,它们对于悲哀的母性都是一种安慰。不过,《药》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那“铁铸一般”的乌鸦最终违逆了夏大妈的意愿,没有飞上夏瑜的坟头,而是“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表明鲁迅在这里并没有以“母性”替代“革命”,“革命”依然在迷信的母亲们的理解之外,也没有以“革命”去否定“母性”,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在“革命”与“母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如果说小说写的是“革命者的救民意志与老百姓的求生意志的悲剧性隔绝”,那么两个母亲的共同悲哀就已经穿越了这一“隔绝”;如果我们不将两个儿子作一种革命∕愚昧的价值上的对立,那么两个母亲的爱就不会因为儿子们身份(革命者、启蒙者∕群众、被启蒙者)的不同而有什么不同。相反,这种悲哀的爱泯灭了身份与价值之差,超越了革命∕群众、觉醒∕愚昧的区分。两个丧子的老母亲带着对儿子的哀悼相伴离开坟场,先觉的革命者(夏瑜)和愚昧的群众(华小栓)的“死”因为两个母亲的“哀悼”(爱)而消泯了价值高低的区分,呈现为共同的人性。在母亲们无言的、哀伤的“爱”中我们不是感受到某种母性的“神性”吗?如此,那挫身而去的乌鸦将两个母亲的视野引向那“远处的天空”,就不再是虚无,也不是那么“阴冷”,而是一个在母亲们的理解之外,却隐含着既是革命的,也是母性(爱)的希望与安慰的所在。可见,在《药》中,“革命”与“母性”之间存在内在的紧张,却并非对立。对于现实中的“母爱”,鲁迅不是一般地肯定或否定。生活中的鲁迅是一个孝子,鲁迅的婚姻是迁就了慈爱的、作为家长的母亲的意志,这使得鲁迅对于母爱有着某种反思。在《<伪自由书>前记》里鲁迅说:“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或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他在给赵其文的信中说:“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从这些话中可见鲁迅对母爱的深思。鲁迅的深刻和复杂之处在于他将母爱放在母性的受难中,放在与“革命(启蒙)”/“迷信”、“现代”/“传统”的张力中来描写。如果说以往我们站在“革命(启蒙)”或“现代(科学)”的立场遮蔽了母性,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立足母性受难的立场返观“革命(启蒙)”与“现代(科学)”:《药》与《祝福》中母性的受难,透露出一个比启蒙、革命、现代更原初的价值和一个更深邃、更本源的世界的存在,而正因为有此一世界的支撑,革命者的牺牲才更显其悲凉意味和悲悯性。“前现代”的母性世界看起来并不理解革命者牺牲的意义(即所谓“隔绝”),却以自己爱的受难包容和安慰了革命者和革命,而在《祝福》中,带给那被狼吞噬了的儿子的安慰的,也只有孤苦无依的母性的“念叨”。这就是母性的力量,一种弱者的“无力之力”。或者说,正因为其脆弱、无用(无效)、被动,才更凸显其力量———通过受难与哀悼的方式。
这与耶稣自愿钉十字架而死所带来的神性的“救赎”有着实质的相通:都源于“爱”的受难,都超越了种种界限与隔绝而通向“无限”,都是对“强暴之力”的批判,也都通过对“死”的最终安慰而呈现出某种救赎性和超越性,一种是宗教性的,一种是非宗教性的。这正是卡夫卡所说的,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的体现。结语:阿长的魂灵如木山英雄所说,寡妇形象、奴隶是鲁迅构筑中国像的唯一基本实体,“民众之悲惨与痛苦的纪念碑”。在鲁迅那里,悲惨与痛苦的母亲不仅让人同情,同时也是批判与救赎的资源:她们首先构成对现实的否定和批判。其次,作为沉默和失声的女性,她们无法解脱的“苦难”本身提出了对“革命”与“启蒙”的反思与质疑。第三,无论是革命者夏瑜还是普通群众小栓、阿毛,他们的“死”在母性的悲伤与哀悼中有了内在关联。母性的悲伤、哀悼(“念叨”)亦成为儿子之“死”的终极安慰,“死”因此有了救赎的可能。而革命者的“血”(死)能否成为真正的“药”,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小栓(和阿毛)包括在死者之中,取决于我们能否理解母性受难的意义,否则就会像鲁迅说的:“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最后想到的死者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的阿长。阿长与《药》中的夏大妈、华大妈和祥林嫂一样,无名无姓,也同样迷信。青年守寡的阿长没有做母亲的机会,作为保姆充当了我母亲的角色(我叫她“阿妈”),将母性完全转移到我身上。不识字的阿长并不知道“三哼经(山海经)”是啥东西,但阿长的母性世界与《山海经》的世界———神话传说、民间信仰(迷信)的世界———是同源的,因为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丰富、博大、神奇又不乏苦难的世界吸引了我,却是我难以把握和言说,也无力改变的。所以我只能“祈祷”(这在鲁迅的作品中可谓绝无仅有)“仁厚黑暗的地母”来安慰这个像地母一样的女性。像鲁迅这样“无所信”的启蒙者和革命者,也许只有通过写作铭刻母性的受难与悲伤,铭刻对受难母性的亏欠和安慰,来寻求自我救赎。受难的母性因此成为鲁迅文学之“罪”与救赎主题的源头之一。
作者:卢建红 单位:广东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 上一篇: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范文
- 下一篇:《学衡》的文学翻译与文化抉择范文